【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
每天早晨或是午後,你不免得會來上一杯咖啡,而你知道這杯咖啡背後藏有著多少咖啡農的心酸故事嗎?
你有沒有想過,手中那杯最頂級且昂貴的咖啡,竟是出自全世界最貧窮的農夫手裡?企業口中的公平貿易真的有落實在農民身上嗎?如果有,那麼為什麼狄恩.賽康又會踏上這一趟9個國家、4萬公里的旅程呢?(責任編輯:徐子捷)

圖片來源:Alla Osipova,CC licensed
文 / 狄恩.賽康
咖啡的內在世界
當你坐下來品嘗一杯美味的咖啡,整個人沉浸其中,感受著咖啡的香氣、滋味、酸度和質地時,你對於這杯咖啡的領會,表面上看來已經面面俱到;然而,在這杯咖啡背後,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一個牽涉到文化、習俗、生態和政治的世界。所有關於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議題:全球化、人口移動、女性和原住民權益、環境汙染、民族自決,都透過你手中的這杯咖啡,在全球各個偏遠的村落裡上演著。
咖啡貿易的體系十分龐大,在產值上僅次於石油。這個產銷網絡極為複雜,全世界目前有五十個生產國、二千八百萬名咖啡農,他們和這個產業鏈最末端的消費者之間,還存在著好幾個層級的中間商,使得這些生產者和你手中的這杯咖啡距離更加遙遠了。
世界上每一個咖啡產區都有各自的咖啡栽種文化。在某些國家,咖啡作物藉由日常生活的宗教儀式和習俗,和當地文化深深地糾結在一起。例如衣索比亞,像塔索.蓋布拉這樣的咖啡農總是以三小杯的咖啡來喚醒他們的每一天,而且只以簡單的炭盆烘焙豆子—咖啡是他們生活的中心,顯然不言自明。
在其他國家,咖啡的意義僅是一種作物,而且還是窮人的作物。舉例來說,你很難在中美洲喝到一杯體面又像樣的咖啡,大多數餐廳只供應隨處可見的「Nes」—和即溶咖啡「Nescafé」同名。
各地的咖啡農有著各自的特色和文化
胡安.瓦爾迪茲(Juan Valdez)是一位蓄著大鬍子、臉上掛著微笑,且穿著乾淨白棉衫的拉丁裔咖啡農,但不是所有的農夫都像他一樣。
各地的咖啡農有著不同的身型、膚色和性別,有些人虔誠地信奉基督教,有些人則是原住民信仰,當然也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烏干達,甚至還有一個咖啡產區的居民是信仰猶太教。
在各式各樣的咖啡文化背後,隱含的是人們對於一些事物根深柢固的理解差異:善與惡、公共責任與個人自由,當然也包括對於神的本質有不同解讀。然而,不論這些差異有多大,他們都夢想著能夠擁有健康、愛、餐桌上的食物、兒童的受教權,以及豐富的幽默感。
我曾經合作過的咖啡農當中,大多數的人不會說當地的主要語言或是官方語言;反之,他們說的是地方方言或是罕見的原住民語言。以拉丁美洲為例,許多農夫不會說西班牙語:在瓜地馬拉,他們可能是說Tzutujil語、Quiche語、Cakchiquel語或其他古馬雅語言;在祕魯,南部人多使用Ashaninkas語,北部人則是說Kechua語。
因此,即便你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走遍整個美洲的咖啡產地之後,可能還是會發現自己一點也聽不懂。在肯亞,官方語言是Swahili語和英語,但是我在中部高原的安布地區(Embu)遇到的農夫都不太會說這兩種語言,而是說Akamba語。至於衣索比亞,其官方語言是一種與希伯來文同源的Amharic語,但我認識的當地農夫則是說Oromifa語。
試想一下,當我第一次拜訪衣索比亞時,雖然認真排練了多次以Amharic 語發表的開場致詞,卻在正式發言時,看到農夫一雙雙無神的眼睛和一個個尷尬的笑容,多麼令我驚訝。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衣著上,即使是同一個社群,服裝風格也有極大的差異。有些地方的社群非常堅守他們的文化和傳統,其中又以服飾占了重要的一角。
在一些國家,如印尼和瓜地馬拉,由於各個農家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當地人會以固定在樹幹的水平背帶織布機來編織衣服。衣服上的圖樣可能已經流傳了好幾世紀,是當地特有的民族風格;或者是在舊的圖樣上加一些新花樣,顯示出該文化的活力和彈性。然而,有時你會發現就在隔壁人家,農人可能正穿著印上耐吉商標或波士頓紅襪隊標誌的T恤,這種現象看似荒謬,但你會發現我們所穿的服裝多半出自全球咖啡產地的成衣廠。
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東部高地的山區村莊,農夫可能總是赤裸著身子,或僅以水牛角雕刻的寶貝套來遮掩性器官,並以一串念珠或牛仔褲裁剪的細長布條來裝飾。祕魯的原住民咖啡農則身披一塊以樹皮染色的布,在臉上紋面;而他們附近的鄰居倒穿得像是來自愛荷華州某個小鎮的人。至於蘇門答臘和衣索比亞的穆斯林,衣著形式就很廣泛,從現代的西式風格,到女性用來包覆頭部和臉蛋的傳統白色披肩都有。
看似規模化的運作,其實仍有許多小農在夾縫中求生存
咖啡生長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肥沃地帶,橫跨赤道以北和以南三十度。這些產地的生態環境從熱帶雨林到沙漠皆有。自從一九五○年代,大規模單一作物生產(或稱「莊園」耕作)的現象愈來愈廣泛。
雖然這些大型農場多半運作得很好,其中仍有許多地方苦於土壤侵蝕和水資源汙染,這些問題常見於大規模單一作物的耕作型態。除此之外,由於農夫大多不識字,在施灑化學農藥時無法閱讀瓶罐上以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書寫的警告標誌,或者是對於使用農藥的知識和訓練不足,經常誤用高濃度的有毒藥劑而不自知。
儘管如此,世界上極大多數的咖啡仍然是透過小農耕作的方法,產自僅有幾英畝的小農場。在許多國家,咖啡農非常注意農作物間作(interplanting)的重要性,為了土地和自己家人的健康,他們會盡力維持多樣化耕作的型態。
在國際環保團體開始注意咖啡生產對於環境破壞的問題之前,這些小農就已經很熟悉「蔭下栽種」(shadegrown)和「對鳥類友善」(bird-friendly)的觀念;這些美麗又豐富多變的地景,容易受到地震、土石流、颶風和海嘯等巨大自然災害的破壞,摧毀農作物、道路、倉庫,甚至威脅到人類性命。
社會經濟情況多變,造成咖啡農民的生活收入大起大落
以生產咖啡為主的社會經濟情況變化劇烈,咖啡農獲得的生豆價格幾乎不符生產成本,當然也不會考慮到對農人來說足以維生或改善生活的合理利潤。相反地,咖啡價格大多受制於成天在紐約和倫敦期貨市場中進出的金融投資者、銀行和跨國企業。
一名咖啡農可能在這個月得到合理的工資,但下一個月的價格立刻暴跌。對他來說,農場的生產水準一點也沒改變,因此他也只能無奈地搖搖頭,繼續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頭五年,咖啡生豆的價格常常跌破生產成本,使得數十萬名咖啡生產者放棄了農地,遷移至城市或出國工作。
有時候,這股被迫發生的移民潮會造成死亡悲劇,例如一群絕望的墨西哥農夫擠上火車離開家鄉時,不慎失足墜軌;或是在德州的酷暑下,被遺棄在上鎖的卡車中致死。
由於這些悲慘的遭遇,有些出自善意的民間計畫和國際組織活動逐漸湧現,試圖為現今的價格機制找到另一條合乎道德的出路,例如「公平貿易」(Fair Trade)。這些努力讓成千上萬名農夫得以留在他們的土地上,繼續靠耕作維生;然而,這也僅占了全球咖啡貿易極微小的部分而已。
即使在價格最好的時期,農村社會也幾乎沒有能力對基本的水利設施、教育、醫療照護和住屋水準有任何實質的改善。問題不只是出在咖啡作物無法為他們創造足夠的收入,還有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困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和國際性借貸組織都極力阻止當地政府對農村社會伸出援手。
這些國家被迫施行「結構調整」政策,大幅刪減農村的醫療照護、環境和教育發展的預算。因此,許多咖啡產地的社區轉向草根性發展,透過自助的努力才能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由此衍生出來的發展計畫、水井建設和地方診所等,相較於其他地方,規模可能顯得渺小,但他們卻能因此獲得立即且直接的生活改善。
咖啡產地與衝突地區的重疊,使每顆咖啡豆顯得更加珍貴
咖啡產地通常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戰爭和戰後餘波會對當地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凝聚力造成深遠的影響。在我曾經工作過的咖啡生產國,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正面臨或在不久之前還在爭取自治或獨立運動,人民要不是在抵抗殖民政府,要不就是受到腐敗或獨裁政權的壓迫。有時候,咖啡農會主動參與這些抗爭活動,例如墨西哥查帕斯(Chiapas)的農民。
至於其他地方如哥倫比亞和蘇門答臘,農夫只是無辜的受害者,衝突的風暴席捲他們的家園,害得他們無家可歸。武裝衝突甚至會讓農夫無法收穫作物,因為辛勤工作一年才收成的咖啡豆會在卡車運送的過程中遭遇打劫,一點也不剩。道路在衝突期間會被封閉,要從一頭橫越至另一頭,必須支付「過路費」給衝突一方甚至雙方。
在帝汶,一位農夫的妻子失蹤;在瓜地馬拉,整個村落的人遭集體屠殺。即使是距離衝突的歷史已有數十年之久的國家,如尼加拉瓜,也可能會因過去的慘痛經驗而再次承受死亡和絕望的悲劇。美國和捷克在該國留下的地雷,或被丟棄在咖啡園裡,或是在暴風雨過後出現在地表,常常炸傷了工作中的咖啡農或是上學途中的兒童,卻沒有人知道地雷埋藏或出現的確切位置。然而,衝突之地有時也可能會變成希望之地,只要長久持續的衝突能結束,就會產生新的政治參與的機會。
文化與習俗、生態與經濟、衝突與創造,這些兩難的問題都糾結在你手中的這杯咖啡裡。最終,各個咖啡社會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和他們」(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將超過這些議題的總和—正是這一切吸引我踏進咖啡的世界。
每一趟前往咖啡產地的旅程都是嚴峻考驗的回報;每一次考察都會對某些為人深信或尚未驗證的信念提出挑戰,也提供自己一個良機以個人力量去參與人們生命有意義的改變;每一次訪問都讓我有機會將自己的技能和心力貢獻給那些種植咖啡豆的農民:他們供應豆子給我,使我能提供頂極的咖啡給顧客,這就是為何我會成為一名「咖啡旅人」(Javatrekker)。
咖啡旅人的演進
事實上,在咖啡產業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業者不曾造訪過任何一個咖啡產地,無論他是烘焙商、中盤商還是咖啡師(barista)。他們對於咖啡農生活的資訊,都是來自於大型咖啡企業的廣告和圖象,像是那位胡安.瓦爾迪茲。即使在那一小群曾經親訪產地的咖啡公司主管和員工之中,也幾乎沒有人會在咖啡園中逗留超過幾個小時;據我所知,更沒有任何人曾經借宿過農夫的家。
有一次,我和一位知名的環保咖啡零售商聊天,我們在爭辯墨西哥南部咖啡產地的營養不良問題,她很生氣地說:「難道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些情況嗎? 我早就大老遠飛去那些村落過了!」如今,有一小群投身咖啡產業的人,對他們來說,咖啡不只是一種商品而已。他們藉著生意之便,沉浸在一個更深層的咖啡世界中,這些人就是咖啡旅人(Javatrekker)。自從一九八七年以來,在咖啡產地之間旅行就是我的生活。
雖然我已經從事咖啡烘焙的行業超過十二年以上,但我進入這個世界的途逕是很迂迴的。在過去,我曾是一名律師兼社會運動者。一方面,我從事主流的法律訴訟;另一方面,我也處理國內外的原住民權益和環保議題。我曾經認為法律是進行社會改革的好媒介;事實上,它可以辦到,只是當時的我還不適合。
我無法忍受文書工作,利用法律耍花招,以及坦白說來,整個司法體制中堆疊起來的組織力量和金錢誘惑。有一回我在蒙大拿的貝克那城堡印第安保留區工作,試圖促使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要求某個金礦公司提出環境影響報告書—該公司是全球採用氰化煉製法提煉黃金的金礦企業中規模最大者。(我們的行動從來沒有成功過!)
在某段很艱難的時期,一位長期投入運動的印第安人查理問我,如果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這個保留區能夠維持多久?如果他們唯一找得到的工作是高危險、低工資的,又會對本地文化造成破壞,那麼不是比完全沒工作要好不到哪去嗎?我們都逐漸意識到,除非改變商業活動的基本運作原則,否則我們付出的心力將只能撲滅因企業貪婪和人們缺乏意識而引起的零星小火。
一九八五年,我進入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對原住民社會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和講課,並且持續在環保和人權議題方面為原住民提供免費的法律協助。在他們的社群之間,原住民對於我的服務口耳相傳,使我得到許多意義深遠的機會,前往許多國家服務和探險。一九八七年,我在羅德島大學以「雨林破壞的原因」為主題,發表了一次演說。
會後,一位教授大衛.阿貝登(David Abedon)與我聯繫,提起了一位他正在經營咖啡館的朋友,打算要創立一個組織來幫助咖啡農,並詢問我是否願意與他聊聊。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咖啡農是原住民,我心想:專注在咖啡產區的發展工作,對我來說似乎是個好機會,可以兼顧我的專業和興趣。於是我們碰面了,三個人很快就成立了第一個致力於咖啡社區發展的組織,名叫「咖啡兒童」(Coffee Kids)。
那位咖啡館老闆比爾.菲斯班(Bill Fishbein)負責籌措資金,我則負責深入各地村落,與咖啡農和他們的家人見面,評估當地的需求,並依照農夫提出的問題來研擬計畫和策略。當時,我真是感到極度開心,這是一個完美的工作(雖然比爾、大衛和我都沒有支薪)。
我們為瓜地馬拉和墨西哥的婦女設立微額信貸銀行(microcredit bank);在蘇門答臘推行一項水利計畫,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行動。總的說來,這是一個穩固的草根性發展。
「狄恩豆子」的產生是為了直接改善農民生活
直到某天,有一件事情改變了我的方向。當時我正在瓜地馬拉構思一項水井計畫,有一家想做慈善公益的咖啡公司願意捐出五千美元來蓋水井。這間公司會照些照片、說說故事,並向消費者吹噓他們的善行,但仍然繼續支付很低的價格給咖啡農。沒有什麼事情會真的改變,但消費者會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那些村落的情況很好,而且整個產業都是在「照顧這些農夫」—如同一位企業主管所言。
我開始思考一件事:如果這間公司只是單純地以實際的價格收購咖啡豆,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也許農人就可以自己負擔興建水井的費用,而不需要仰賴公司的「善行」了。
如果這間公司願意對他們收購豆子的產地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直接參與當地的發展工作或以其他形式支持這些社會,會發生什麼事呢?貧窮的趨勢,看來似乎是咖啡生產的地方性問題,人們能否挑戰它和克服它?如此一來,這間咖啡公司是否能繼續獲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他公司又能找出什麼理由不跟著這麼做呢?就在這一刻,我的思緒都清晰了,於是「狄恩豆子」(Dean’s Beans)也隨之而生。
一九九三年,我只有一小台烘豆機和八袋咖啡豆,就這麼開始了我的事業。當時我將一部分時間挪去教書,同時也接一些訴訟案件。因為我很清楚使用農藥對於第三世界的環境和農夫健康的影響,所以我只買有機咖啡豆—許多常施用在咖啡豆上的農藥在美國是被禁用的。
此外,我也只向小型農場和以原住民為主要成員的合作社收購豆子,這些原住民全都努力地在這個對他們充滿敵意的世界中試著維持固有文化和尊嚴。全球市場的結構和價格反映的是,一個世紀以來的不平等待遇,使得咖啡產區停留在未開發的狀態。提供發展上的援助和行動主義是彼此建立關係的關鍵,我也將繼續旅行,服務我終身所愛的土地和原住民。
狄恩豆子的理想和咖啡的品質迅速地成為我們追求的主要目標。我們以緩慢、穩健的步伐成長,並以良心經營。許多人說我們是「咖啡產業中的Ben and Jerry’s」,但是那間公司很快地就轉型成一間由跨國企業掌控的大公司,最初的創始人雖然口袋滿滿,卻很不開心。
所以,不了!我可不是為了成為一個「使之茁壯,繼而求售」的百萬富翁,才投入這個事業。我也不想將我的「社會責任」兌現,讓新的經營者對大眾維持固有形象,卻挖空了這間公司的核心原則—這是現今許多「進步」的企業常見的動態。
不是憐憫,而是尊種的新商業模式正在運行中
我想要試著發展一種立基於尊重、道德和正義的新商業模式,證明它是可行的,不但能夠養活我的家人和員工,還能享受過程中的快樂。這個模式也必須是靈活彈性的;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積,我們發現任何需要調整的問題—不論是關於發展、產品定價,或是任何牽涉到我們與農夫之間關係的事情—都必須要能夠改變行事途徑才行。
因此,我們必須投入更多心力在過程更甚於結果,這種彈性的工作方式讓我的主要企業夥伴都快抓狂了,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事先擬定好計畫和成長目標。
之後我開始和咖啡產業中志同道合的人見面。一九九八年,我們一共七人在亞特蘭大一起成立了「咖啡合作社」(Cooperative Coffees),這是全球第一個由咖啡烘焙商組成的合作社。
我們聯合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讓我們得以在公平貿易的條件下,以團體身分向產地直接購買,並且可以一起致力於改善公平貿易體系;其次,我們意識到彼此都是同路人,在這個很少有人結合商業活動與社會正義的產業中,我們正走在同一條道路上—我找到了同是咖啡旅人的夥伴。
身為咖啡旅人,我們愈來愈融入農夫的艱辛生活;我們每一個人投入的程度各自不同,並且也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於正義和誓約的信念。當然,世界上還有很多咖啡旅人。
相較於許多人僅將咖啡視為賺錢生意,並且認為壓榨農人只是一種讓利潤最大化的方法,咖啡旅人可能是想法新穎、具關懷胸襟的中盤商、進口商或烘焙商。在過去十年之間,整個咖啡產業看起來是在進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咖啡旅人的影響力,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現在,我邀請你再喝第二杯咖啡(第一杯咖啡想必早已喝光或變涼了)。你是否準備好進入這個隱身在你杯子當中的世界呢?
跟著我前往全球各個咖啡產區吧!體驗他們的習慣、文化、掙扎和希望,了解咖啡旅人如何參與咖啡農的生活,又如何融入當地的社會。你即將讀到的故事有時候是令人樂觀的,有時候則是令人悲傷的;有一些故事很幽默,有一些則發人深省;最重要的是,書中的所有故事都是非常棒的旅行冒險。
深深地喝一口,你的咖啡嘗起來將永遠不再一樣。
推薦閱讀
你手中那杯香濃咖啡的成分如下:咖啡農被七百萬地雷炸斷手腳、失去雙眼光明
咖啡價錢為什麼差這麼多?神分析星巴克、City Cafe 和罐裝咖啡背後的消費心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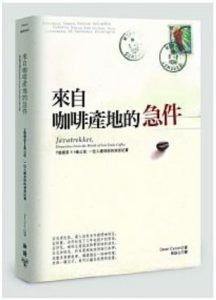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由臉譜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Alla Osipova,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