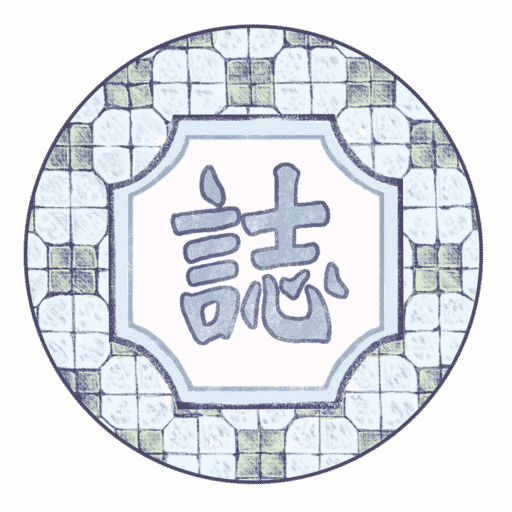1997年6月30日夜晚,香港滂沱大雨,解放軍連夜從邊境進駐香港。陳果手頭還有一些底片沒用完,臨時拉上3、4人就去上水一帶拍軍隊入城。他當時還不知道拍來做甚麼,只讓演員李璨琛在暴雨中走來走去。後來才加入警察埋伏看軍隊的市民、誤把西瓜當炸彈的情節,這一真實現場從此成為《去年煙花特別多》的珍貴畫面。
25年後,2022年6月的香港暴雨連月,陳果說現在說話都要小心,現狀不多談。不如說說從前,從前拍戲,他小本製作,臨時起意,咩都敢死。
拍《香港製造》的高潮一幕,李燦森飾演的主角中秋在屋邨發現好友阿屏已病逝,憤怒地將一部電視機從沙田瀝源邨的天井扔下。這場戲沒事先申請。拍攝時李璨琛很害怕,不敢扔,上了七樓,陳果說不夠高啊,又再上五、六層。
「大佬,掟啦!」陳果和拍攝團隊在下面看着,向樓上大叫,李璨琛終於出手。
轟一聲,一台舊式電視機在天井地面巨響炸裂,「拍完便走,屍骸也沒有拾回,以免被人拘捕。」

本土和自身危機
電視機炸碎的那年,是1996年的香港,也是陳果盡地一鋪的一年。
九七前數年,他陷入嚴峻的個人危機。當時年近40,已隨電影工業打滾10多年,常常做副導演、策劃。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他執導了兩部電影《大鬧廣昌隆》和《五個寂寞的心》,前者被雪藏3年,後者根本沒有上映,「被當作沒有發生過」。
「我跟隨整個主流工業,你叫我拍我就拍,你叫我做導演我就做,沒有自己的。如果我無自己嘢我會死㗎喎!」他這樣剖白。
港產片其實素有時代觸覺,九七前後,影射中港關係或港人危機的電影不少,普羅大眾熟悉的有《表姐,妳好嘢!》和《國產凌凌漆》,不過陳果認為,這些電影的內核不是時代狀態。

「電影界都是搵食,其實用得最多的是張堅庭、周星馳,那些諷刺式的,一些片段放在他們的作品裏,《表姐》好鬼好笑。但這些都是過眼雲煙,是時代背景下,看見某些狀態然後放進作品,它不是作為一個中心點去發展,都是一個過場或用一個人物來搞笑,沒有甚麼政治性。」
陳果想做的不一樣。他把時代狀態化作整部電影的氣氛,一些靈感來自他所欣賞的日本導演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
陳果1995年開始寫這劇本,故事圍繞幾個偶然相遇的沙田公屋少年而展開:中學生中秋讀書不成,又愁家庭破碎,混跡古惑仔,他的跟班阿龍有智力障礙,總被人欺負;兩人收數時結識了患有絕症、等待換腎的女孩阿屏,在末世氛圍中,3個少年成了朋友,一同找尋另一名跳樓少女寶珊生前的痕跡……
故事的背後,是陳果感受到的劇變香港。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種很懶理的態度,不是逃避,是很事不關己。」陳果說,大人盤算着移民還是賺錢,沒甚麼人關心年輕人,也覺得年輕人不明白。表面上中港之間多了互動,陳果去酒樓吃飯,經常見到從內地來港學師的人,他的朋友也開始北上工作,有人在內地有了另一頭家,就和香港老婆離婚。
「隱藏的危機便是香港本土的危機,因為其實香港移民潮也來了幾次,每一次都走一批人,所以我便用這種感覺構思年輕人中秋的家庭背景。」陳果說。《香港製造》中,中秋的父親北上工作後另覓新歡,阿屏也沒有父親,這種無父的狀態被認為是隱喻無根香港。

《香港製造》的所有角色都沒有直言回歸或政治,但一股壓抑的大限氣氛卻無所不在。陳果大膽地把「香港文化一部分」的跳樓現象貫穿全片,少女跳樓的畫面反覆閃現,而中秋想做場大事卻懦弱而歸,最終走向自殺的一幕,回應了時代的冷漠。
1996年,他拿着50萬投資,再加上不久前和劉德華合作後留下的四萬呎過期底片,開拍《香港製造》,錢實在太少,戲中所有演員均由素人非專業演員出演。
戲拍到一半,不夠底片,他找了所有認識的電影公司,捐過期底片給他,別人公司雪櫃裏的底片都被他搗騰出來。
不出所料,當時香港人對這部電影的態度也是懶理。它於1997年上映,本地票房僅有119萬。陳果另闢蹊徑,帶着作品去一個又一個國際電影節,這齣打正香港旗號的獨立電影在大時代背景下一致好評,也讓陳果一舉成名。

1997年,它在瑞士洛伽諾國際影展、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西班牙杰桑國際青年電影節和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穫取不同大獎,並最終斬獲金馬獎最佳導演和最佳原著劇本。
「我記得我與Sam Lee (李璨琛,飾中秋 )去洛伽諾影展,你在廣場中,八千多人看你齣戲,那種震撼好得人驚,很有鼓舞性。你於是蹦蹦聲、突然一夜之間成長。」
他從此發現脫離主流的可能性,發現原來電影這樣拍才過癮,也發現原來香港可以這樣拍。「嘩,如果是這樣,香港真的有好多東西可以拍!」在九七大限前,陳果找到了自己。
砵蘭街這個「元兇」
陳果父母是漂泊的華人。母親是馬來西亞華僑,父親是泰國華僑,1949年,他們回應「祖國召喚」,被新成立的共和國吸引,去海南島參與建設。陳果在海南島海口市長大。看着知青下鄉,文革爆發,父母終決定離開。
香港本來不過是中途站。約莫1969年,他們落腳香港,原在盤算去泰國抑或馬來西亞,但不知不覺就留下了。當時香港正急速騰飛,遍地機會,再去南洋又是一場冒險。
說起自己與香港的關係,陳果第一句是「很僥倖我們沒有離開」,遺憾的是,當年讀書太少。
「趕着就開始做童工,我沒有怎樣讀書,讀到中一、中二左右。」他後來輾轉進入電影工業,從低做起。
他自稱香港電影的社會派,和學院派相比,總感覺一些想法沒有那麼高超,別人懂得留白,他總是「講白了一些」,這是他的缺陷,但正正也是這種粗野、直接和暴力,成就了陳果。
香港文化骨子裏從來不是陽春白雪,而是龍蛇混雜,野蠻生長,亦莊亦諧。香港就是這麼出乎意料,陳果說,就像當年在黃賭毒俱全的砵蘭街,一座唐樓2樓,竟有一個民間力量籌組起來的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它於1978年創辦,辦電影夜校課程,匯聚嚴浩、陳樂儀、徐克、磊懷、唐基明、鄒長根、蔡繼光、羅卡、舒琪等一眾導演擔任導師,也策劃許多電影文化活動。

陳果與許多社會派電影人都在這個電影文化中心半工讀。那也是香港新浪潮爆發的時代。「香港(電影)在七十年代已經發展得很厲害,但問題是八十年代開始更加厲害,新浪潮電影開始爆發,結合西方電影的技巧,令香港電影澎一聲,與以前那種打戲很不一樣。所有的起飛都是那一兩年,78、79年。」
在電影文化中心,陳果受到前所未有的薰陶,「我在那裏看很多Art house以及獨立片,大島渚也是在那開始看。入了行之後我也繼續看,這也是為甚麼走了這條路的一個『元兇』。」
在砵蘭街,意外落腳香港的小子感受到電影與香港的魔力。九七前夕,他曾經想過出國進修電影,但總感覺走了之後再回來,「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
「不要記得,甚麼也沒有發生」
他之後拍香港拍得愈發起勁,數年間完成了「九七三部曲」在北角東寶小館吃飯時,他認識了一些華籍英兵—— 隨着香港回歸,過千名華籍英兵被港英政府拋棄了,大批人中年失業,「個個都在呻 (他們都在抱怨)」。陳果把這些憤怒中佬寫進《去年煙花特別多》。相比《香港製造》中的少年,這部戲中的主角似乎更加清醒,意識到自己成了「香港孤兒」。

香港三部曲最後一齣《細路祥》,陳果把鏡頭拉回砵蘭街,從在茶餐廳長大、日日幫家人送外賣的祥仔眼睛出發看香港。在街頭巷尾,祥仔認識了內地偷渡來港的小人蛇阿芬,在1997年回歸前夕新馬師曾去世並引發爭產的社會氛圍下,兩個小孩發展一段友誼。片中的祥仔再次呈現無父狀態,與父母都不親近,反倒與外傭姐姐更為親密。
「這10年另計,過去的50年香港人是不愛香港的,只有我們這些人愛香港。因為我們千方百計離開了我們的原居,來到這裏,我們覺得這裏很好住,我們要在這裏生根,我們愛這個地方比原本在香港的人多,老老實實。」
對於香港,陳果有一種尖銳的愛。難怪學者史書美指出,陳果的電影既是、也不是香港寓言,「九七三部曲」細緻描繪港人狀態,但同時又可以被看成是一份反對香港集體身份的宣言。而學者彭麗君則說,陳果的作品像一個彆扭的愛人,不會簡單地給觀眾他們想要的東西。

《去年煙花特別多》走到最後,主角家賢中槍後失憶了。陳果說,那是他有意為之的,對時代狀態的一種回應。
「寧願失憶也不去記住,在戲中是一個Good Point,我當年的想法是:橫掂你都唔知點樣 (橫豎你都不知怎樣),不如忘記好過啦,不要記得,甚麼也沒有發生,可能這樣你更加瀟灑地面對現實或者面對將來。」
那麼《香港製造》的中秋,可是那個逃避大限的香港?陳果一句否定,有意識的才叫「逃避」,當時的香港是懵懂不知,那種狀態他總結為:「乜撚都唔撚知,乜撚都唔撚識!(甚麼也不知曉,甚麼也不懂)。」
遲來的覺醒
陳果說:「香港年輕人遲了20年發育。」
你指哪代年輕人?「以前那一代,代代也一樣。現在只是因為這幾年的東西令他們提早,催谷了、快了。」近10年,香港社會更多談及身份認同,他覺得這是「遲來的覺醒」,「有少少瞓醒」,但瞬間又被打沉了。痛苦的是,香港人已無法失憶。
還是說當年吧。《細路祥》還未拍完,他就開始了《榴槤飄飄》,同樣在砵蘭街一帶。這時候陳果愈發放鬆,《榴槤飄飄》沒有完整的劇本,他一邊拍一邊在街頭蒐集資料。
「那時還仍未起朗豪坊,整條街也是陰陰沉沉,那時候的風景是很好看的,真的很好看。」當年大家總以為50年很遙遠,但轉眼香港風景就走到了下半場,《榴槤飄飄》陳述的主角已經從茶餐廳的祥仔變成了內地來的阿芬。

兩小無猜在海邊爭論「香港是誰的」,那種風景已成過去。
去內地發展數年之後,陳果返回香港。近年他在《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三夫》、《鬼同你住》中嘗試了不同風格,褒貶不一,但有甚麼所謂?只要拍得過癮。
「當然我不知道我將來會怎樣,但是人生苦短,有時沒甚麼所謂,只要拍一些過癮的東西。」他說近來想拍與移民有關的故事,但變得思前想後。「其實作為一個見證應該留下記錄,不過也算了,唉,你不能說那個氣氛,無論用甚麼方法去說那個氣氛,也很容易犯罪……」
還是不說了。年過60,陳果對這城看得透徹。一些事情他一直覺得就會這樣發生。
「香港一定會繼續痛苦下去,何解呢?無解的。怎樣救?救不了,解決不到。」他自言自語,圓框厚鏡片後的眼神沉重起來。
(原文刊載於2022年《Side B》ISSUE 02 九七電影大限)
參考書籍:
彭麗君《黃昏未晚 後九七香港電影》
朗天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
朗天 《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