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好在哪?
84 个回答
谢谢邀请~
好在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只属于自己的城市。
这是一本短小的,像梦境碎片一样轻盈和意义纷繁的书。不过,卡尔维诺没有把散落一地的拼图推到读者眼前,而是通过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所作的一系列旅行汇报,以及开篇别致的标题结构,尽力创造了一个有开始有结尾的空间,好让我们能发现些什么。这是一本像多面体一样的书,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

目录,[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 译,译林出版社,2006
而他所使用的语言,又是这样美:
在帝王的生活中,总有某个时刻,在为征服的疆域宽广辽阔而得意自豪之后,…… 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在黄昏时分袭来,带着雨后大象的气味,以及火盆里渐冷的檀香木灰烬的味道。……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蚁蛀食的精雕细刻的窗格。
这本书像一座迷宫,也像一个游戏。卡尔维诺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
《看不见的城市》所创造的55座城市里,有三座是我最喜欢的:一座是瓦尔德拉达,一座是珍茹德,还有一座是埃乌特洛比亚。
先说瓦尔德拉达。这是一对像镜城一样的孪生城市,一座在湖畔,而另一座是它在湖中的倒影。湖畔的瓦尔德拉达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水中的那个城市完整地再现出来。最有趣的是:
瓦尔德拉达的居民都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镜子里的动作和形象,都具有特别的尊严,正是这种认识使他们的行为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即使是一对恋人赤身裸体地缠绕在一起肌肤相亲时,也要力求姿态更美;即使是凶手将匕首刺进对方颈项动脉时,也要尽量使刀插得更深,血流得更多,因为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交合或者凶杀,而在于他们在镜中交合或者凶杀的形象要冷静清晰。
镜子外面似乎贵重的东西,在镜子中却不一定贵重。
两个瓦尔德拉达相互依存,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

Ponte vecchio, Florence, Italy
第二座城市珍茹德是这样的:
是观看者的心情赋予珍茹德这座城市形状。如果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你对她的认识就是自下而上的:窗台、飘动的窗帘、喷泉。如果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你的目光就只能看到路面、水沟、下水道口的盖子、鱼鳞和废纸。你无法说这种风貌比那种更加真实。
这有点像王尔德所说的「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了。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有些人看见了天上的星星。」
第三座城市埃乌特洛比亚,简直就是《模拟人生》:
如果有一天,埃乌特洛比亚的居民厌烦了,再也忍受不了他们的工作、亲属、房子、街道、债务,以及那些他们必须打招呼的人和对他们打招呼的人,全城市民就决定迁移到临近那座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崭新的空城里,在那里,每个人都开始从事新的职业,娶一位新的妻子,打开窗户就能看见新的景致,每晚跟新的朋友做新的消遣,谈新的闲话。于是,他们的生活在一次次搬迁中不断更新。多样化的职业保障了人们工作的多姿多彩,以至于极少有人能在人生之中重复已经做过的工作。
……
在读到「这里的建筑都有镶满海螺贝壳的螺旋形楼梯」的城市伊西多拉时,也许有人会想到腓特烈二世时期普鲁士新宫的贝壳厅,或是巴塞罗那的高迪的巴特略之家;在读到有着「大铜钟、理发店的条纹窗帘、九眼喷泉的水池、卖西瓜的货亭、隐士与雄狮的雕像、土耳其浴室、街角的咖啡店、通向海港的小巷」的城市左拉时,也许有人会想到意大利有着九十九孔喷泉的阿奎拉,或是电影《美丽人生》里罗伯托·贝尼尼骑着自行车穿过的托斯卡纳小城阿雷佐的街巷与广场;在读到「入夜后围着集市四周点起篝火堆,坐在布袋或大桶上,或者躺在成叠的地毯上,聆听旁人所说的词语」的城市欧菲米亚,也许有人会想起《一千零一夜》;而读到「只有通过她变化了的今日风貌,才唤起人们对她过去的怀念,而抒发这番思古怀旧之情」的城市莫利里亚时,也许有人会想起老北京城。

不过,诚如1983年卡尔维诺在哥大的一次讲座上所说的,「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想表达的想法一种,正是让读者小心不要陷入词与物、名字与真实的对应和隐喻的迷雾中。尽管如此,关于某座城市的记忆和联想,会在阅读过程的某个瞬间,像一道闪电一样,突然照亮我们的脑海。这种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就是「读出只属于自己的城市」的体验。
卡尔维诺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说:「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这种非常个人的、私密的、情绪化的、不可言传、却又在后来的某个时刻似曾相识的体验,正是这本书的魅力之一所在:
你的脚步追随的不是双眼所见的事物,而是内心的、已被掩埋、被抹掉了的事物。如果你觉得两个拱廊之中的一个更为惬意,那是因为在三十年前曾有一个穿绣花宽袖衣服的姑娘走过那里,或者是因为那个拱廊在某一时刻里的光线使你联想起另外一个地方的什么拱廊。
在书中,马可·波罗说:「每次描述一座城市时,我其实都会讲一些关于威尼斯的事」。某个奔波颠沛讨过生活的城市,某个吹着晚风游荡过的城市,某个遇到所爱又失去所爱的城市,还有那些「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还有叶脉一样的城市,手纹一样的城市,能够看透其晦暗、虚构的厚重的金银镶嵌的城市」,或是那些「三千人演伪君子,三万人演寄生虫,十万人演流落街头等待机会恢复地位的王子」的城市,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吧。
回到正题,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好在哪?
在看得见的城市里,《骆驼祥子》是祥子的北京,《城南旧事》是林英子的北京;《倾城之恋》是白流苏的上海,《长恨歌》是王琦瑶的上海;《源氏物语》是平安皇族的京都,《古都》是千重子和苗子的京都;《巴黎圣母院》是埃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的巴黎,《高老头》是拉斯蒂涅的巴黎;《雾都孤儿》是奥利弗的伦敦,《福尔摩斯探案集》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伦敦。
而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写道:「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看得见的城市与看不见的城市,并无高下之分。对于个体而言,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与自己有了某种特殊联系的一瞬间,产生了意义。我们正在做着和忽必烈一样的事情:
「现在,每当马可·波罗描绘了一座城市,可汗就会自行从脑海出发,把城市一点一点拆开,再将碎片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
有些书带我们看到他人的世界,有些书带我们看到自己的世界。
《看不见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今天给公众号写的导读文章,顺手一起贴过来

| 对「经典」我们有什么可说?
「尸解」这样的略带重口的名字,当然不单是为了哗众取宠。更多的,是因为它最接近于事实本身。正如卡尔维诺自己所说:「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学校却倾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这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识得比文本自身还多」。
一本「经典」就是一座搭建完成的纸牌塔,施力和受力都刚好处于平衡状态,一种自我满足(艾柯语)的完成式——文本通过其自身,把想说的话,已然说尽,把欲求传达的意义,已然昭示。「经典」作品只能作为整体被理解,任何另行一文妄图加以阐释的尝试,在我悲观的看来,都必将对这种精妙的平衡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解读「经典」注定是一场顾此失彼的艰难选择,就像要向众人展示一种生物的内部结构,唯大刀阔斧、开膛破肚这一路可走。
所以,请记住,所有导读永远永远都不可能代替「经典」本身,它只是引人通往「经典」的众多道路中的一条。
| 关于作者

伊塔洛·卡尔维诺出身于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之家,父亲是在大学执教的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弟弟是地质学教授,连两个舅舅也都是化学家,要命的还娶了两个化学家的舅妈。在这样的理科之家,卡尔维诺自嘲是「家中败类」,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
如果对卡尔维诺的文学造诣,你还不甚了解。那么,我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客观评价:卡尔维诺在世时,瑞典文学院没有跪在他面前,求他收下诺贝尔文学奖,是诺奖永久地、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份跪求名单,起码还应该包括托尔斯泰、博尔赫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纳博科夫、沈从文以及鲁迅......世界上最重要文学奖的评委们,也常有犯糊涂的时候。
看不见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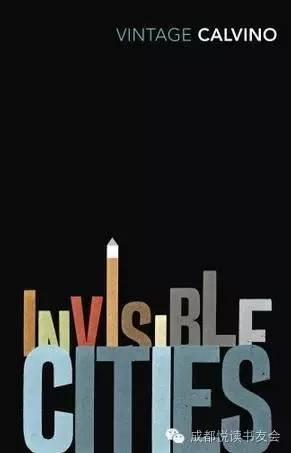
| 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这个太过文艺的小标题不是我取的,是卡尔维诺自己顶着鸡皮疙瘩说的,他说: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
没错,《看不见的城市》无疑是本「诗的书」。在这本书中,作为文学基本构件的语言成了神秘试验的原材料,被装进试管和烧杯混合加热,伴着炼金术士的偏执,反复提炼,最终萃取出薄薄一百来页的小书——一本短篇小说。
写一本短篇小说有多难?这让我回想起上小学每次写作文的苦,为了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都是有字数要求的,三年级以前要求必须写到300字以上,对于小学生的我来说,简直相当于一场万米长跑,每次写出一小段立马停下来数字数,东拼西凑终于迈过终点线,马上鸣金收兵绝不恋栈,古人不是说一字抵千金,才不会那么容易便宜老师一个"以上"呢。后来,随着年级的升高,字数要求层层加码,变成500字、800字、1000字,对于我这种不善言辞,又尚未掌握作文技巧的小学生来说,每次都苦不堪言。当时要是有同学怀揣以后靠爬格子赚钱的梦想,几年下来,也消磨殆尽了吧?直到升上初中,有次语文老师对我们抱怨字数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觉得要求字数很难,其实作文字数要求少更考功底」,当时心里面的想法有两个,一是不明觉厉,二是跪求老师提高难度。
单从技艺上讲,把文章写短的确很难。长篇小说能够以诸多感觉,众多忧伤和欢乐使我们受到作品的感染。长篇小说家可以慢条斯理地写,他有足够的空间转来转去,营造氛围,酝酿感情,既便有一两处失败,对于全局也并无大碍。漫漫长篇,换个角度重新再来又有何不可。但是对于短篇小说家来说却必须做到简明、凝练以及精巧,所有的元素都必须进行有力的压缩。如果把写小说比作投箭入壶,长篇小说家可以有上百次机会,而短篇小说家只有一次,不成功,便成仁。
回到《看不见的城市》,翻开小说你会发现这本书被无处不被既精准又模糊、充满意象、富于情感的结晶所覆盖,彼此之间用具有节奏感的蜘蛛丝串连,融为一体,在关于城市的想象、象征、寓言和隐喻的空间中,展开对异域都市的描绘。语言的精练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另一种由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当语言被提炼简约到一字不可删的状态,美妙的化学反应就此产生,读《看不见的城市》,近乎于读诗:
一个人在荒野驰骋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会渴望一座城市。
终于,他来到了伊希多拉。

▲ 伊希多拉 (城市与记忆 之二)
启程,在六天七夜之后,你会抵达白色之城卓贝地,
全城在月光笼罩之下,街道宛若一束纱,缠绕在一起。

▲ 白色之城 卓贝地 (城市与欲望 之五)
你愿意相信我,那很好。
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造的。

▲ 蛛网之城 奥塔维亚 (轻盈的城市 之五)
| 建筑般的结构、几何式的完美
《看不见的城市》最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它建筑般的结构和几何图像的美。卡尔维诺奇妙的形式和他有名的“轻盈”,如同作家的金字招牌被广为传颂。遗憾的是,这些特征在读者群体中逐渐变成对作家的刻板印象,高墙似的阻挡着读者对卡尔维诺作品更深入的探索。形式的美妙,终究只是为赋予手中材料以组织结构,而抛开卡尔维诺作品内在的丰富,“轻盈”毫无意义,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卡尔维诺的轻是夸父的轻,是一个瘦子饮下大江大泽后的轻盈。
《看不见的城市》由两大部分交替构成,其一是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之间的对话,在文中以斜体字印刷;其二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描述他旅途中所经城市。全书共9章, 每一章的开始和结束是两人的对谈和诘问, 正文共讲述了55个城市, 涉及11个主题, 每一个主题都包含5个城市。这11个主题分别是:城市与记忆(A)、城市与欲望(B)、城市与符号(C)、轻盈的城市(D)、城市与贸易(E)、城市与眼睛(F)、城市与名字(G)、城市与死者(H)、城市与天空(I)、连绵的城市(J)、隐蔽的城市(K)。
卡尔维诺最初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每一个主题都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当这些文件夹被渐渐装满时,关于城市的篇章像砖瓦一样,被打乱、重新组合,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在每一个主题写到第二个城市时,就引入一个新的主题,然后有条不紊地按顺序依次递进。如果我们用字母来表示主题, 用数字来表示主题序列, 例如用A1表示城市与记忆之一,那么第一章的小节题目就是:A1A2 B1A3B2 C1A4B3C2 D1。
对于这种结构,卡尔维诺是这样解释的:「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于是「泥瓦匠」卡尔维诺便在堆砌的过程中,每到固定的间隔,就加入新的建筑材料。最后,连小说的目录都显现出一种建筑的对称性和稳固感,以及城市的精巧布局和完美的几何对称结构。


即使后来写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些意象和结构都更为复杂的作品之后,卡尔维诺在诺顿讲稿《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依然略带偏爱的认为,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含义最丰富的仍然是《看不见的城市》,因为在他这本书中把他的各种考虑、各种经历与各种假设都集中到同一个形象上。这个形象像晶体那样有许多面,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和主从关系。它又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
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每个概念和每个标准都有两重性,概念与主题「相互交替,相互交织」,正如城市里蜿蜒曲折的街道,城市间笔直宽阔的乡道,一条街引你走上引一条街,一条大路让你从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城市。小说的繁复性,以及因繁复所展现出的空间性,进而构成的对城市形象的模仿,还不止是限于表面形式上。如果再继续深挖就会发现,《看不见的城市》在章节主题的指涉上,也潜藏着相互交织的线索,每一条线索都是向外延伸出去的路,拓展小说创造的空间,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可能性。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城市与记性这样的主题指向的可能是欲望:
在他盼望着城市时,心里就会想到所有的这一切。因此,伊西多拉便是他梦想中的城市,但只有一点不同。在梦中的城市里,他正值青春,而到达伊西多拉城时,他已年老。广场上有一堵墙,老人们倚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记忆。

▲ 伊希多拉 (城市与记忆 之二)
城市与眼睛的主题,指向的可能是轻盈:
在树林里走上七天,去宝琪的旅人还见不到城市的影子,其实他已经到了。地面上竖起的一根根高高的细长支架一直穿进去层,它们间隔很远,支撑着上面整座城市。登上云梯,你就能走进城市。那里的居民极少下到地面来,

▲宝琪 (城市与眼睛 之三)
城市与贸易的主题,指向的也可能是记忆:
到欧菲米亚来决非只为做买卖,也是为了入夜后围着集市四周点起的篝火堆,坐在布袋或木桶上,或者躺在成叠的地毯上,聆听旁人所说的词语,诸如「狼」、「妹妹」、「隐藏的宝藏」、「战斗」、「疥癣」、「情人」等,篝火旁的每个人都要讲述一个关于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和情人的故事。当你离开欧菲米亚这个每年冬夏至和春秋分都有人来交换记忆的城市时,你知道在归程的漫漫旅途上,为了在驼峰间或平底帆船舱内的摇摇晃晃中保持清醒,你会再度翻出所有记忆,那时你的狼会变成另一只狼,你的妹妹会成为另一个妹妹,你的战斗也变成另一场战斗。欧菲米亚是个在每年冬至和春秋分交换记忆的城市。

▲欧菲米亚 (城市与贸易 之一)
总之,这是一座没有官方推荐的旅游路线图的城市,它邀请甚至鼓励读者化身成「漫游者」,尽情依照自己的喜好,在城市间游荡,顺着一座城市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到进入下一座城市的钥匙,或者干脆直接享受迷路和发现的乐趣好了,或许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者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
|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关于地狱的城市
卡尔维诺借马克·波罗之口讲出小说的目的和奥秘: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方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地警惕和学习:在地狱中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男神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里讲过一段话,我深以为然,
我们能感受的,远远超过我们能思考的,又远远超过我们能讲得出来的。
可感的世界真的比可知的世界大太多了,概念思维只在可知的世界进行,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常听说,问题比答案重要,问对问题答案自然就跑出来了,原因在于从问题到答案,在可知的世界之中,就只是推理演绎一条坦坦大道而已,跑都跑不掉。
虽然这段话是在说,概念思维与实体思维的区别,但是这段话的前半段同样非常准确的击中了关于小说的奥秘,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如果要写一个女人跳轨自杀的故事,一篇新闻报道的篇幅足够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警示教育意义讲得一清二楚,何苦去写(读)一本洋洋洒洒厚近千页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作者在用文字搭建一套VR系统,把人最细微、最难以捕捉的感觉精准还原给读者。
同样的,《看不见的城市》这本关于城市的爱情诗,即使你不能即刻领会卡尔维洛想借由文字传达的深意,但是你读到这样的文字,一定能感受到卡尔维诺向读者营造的,可感知可体会的东西。在阅读中,不经意间被小说某一个片断或者许多片断精确地击中,为之一振,即便不能准确的复述出一个所以然来,也会停下来会心一笑,不信?
某天清晨,当你在阿纳斯塔西亚醒来时,所有的欲望都会一起萌发,把你包围起来。这座城市对于你好像是全部,没有任何欲望会失落,而你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由于她欣赏你不欣赏的一切,所以你就只好安身于欲望之中,并且感到满足。阿纳斯塔西亚,诡谲的城市,拥有时而恶毒时而善良的力量:你若是每天八个小时切割玛瑙、石华和绿玉髓,你的辛苦就会为欲望塑造出形态,而你的欲望也会为你的劳动塑造出形态;你以为自己在享受整个阿纳斯塔西亚,其实你只不过是她的奴隶。

▲欲望之城 阿纳斯塔西亚 (城市与欲望 之二)
到达特鲁德时,若不是看见特大字母拼写的城市名字,我还以为是到了刚离开的飞机场呢。他们驱车送我经过的郊区跟其他地方的郊区别无二致,都是一些黄黄绿绿的小房子。循着同样的路标,穿过同样的广场,绕过同样的花坛。市中心的街道陈列着同样的商品、装潢和招牌。
...
你为什么来特鲁德?我问自己。
我已经想启程离去。"你随时可以启程而去,"他们说,"不过,你会抵达另外一座特鲁德,绝对一模一样:世界被唯一的一个特鲁德覆盖着,她无始无终,只是飞机场的名字在更换而已。"

▲特鲁德 (连绵的城市 之二)
还有每次我面对「塑造人生的××本书」或者「哪几本书改变了你的价值观?」这样的书单和问题时,就会想起下面这段对话:
马可·波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描述一座桥。
"可是,支撑桥梁的石头是哪一块呢?"忽必烈汗问。
"整座桥梁不是由这块或者那块石头,"马可答道,"而是由石块形成的桥拱支撑的。"
忽必烈汗默默沉思了一阵,然后又问:"你为什么总跟我讲石头?对我来说只有桥拱最重要。"
波罗回答:"没有石头,就不会有桥拱了。"
| 小说是险恶的桃花源
如果我说小说家们干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你会不会觉得我吃错药了?当然,小说这个行当从古至今都是自由的乐园,你只需要稍稍具备想象力和说故事的能力,小说之门随时随地向任何人敞开。它没有拒绝过盲目的吟游诗人、循规蹈矩的保险公司小职员、抛家弃子的自私鬼、生性孤僻的美国老头,还有半路缀学的未来律师。如果你不指望靠它养家糊口(除开赶上网络好时代的今天,其他小说作者要靠它养家糊口也真不容易做到),甚至可以不需要读者,吃饭工具也简单到寒酸,有纸有笔,随时开工。
但是在小说界,在总有那么少数人不安现状,一心想要探求这一片和谐的背后还有什么。于是,小说的乐园变成一座倒置的桃花源,初看豁然开朗,环顾左右,人人怡然自得,复行数十步,就到极狭才通人的地步,再往前行可能就是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
小说家到底想要探求什么呢?在《看不见的城市》中,通过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的对话,卡尔维诺将现象学之父胡塞尔提出的欧洲人性危机问题摆在了读者面前。欧洲人文危机是胡塞尔在上世纪初期对理论科学与生活世界割裂的深刻焦虑,昆德拉甚至认为「胡塞尔谈到的危机在他看来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问欧洲是否有在这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
胡塞尔所谓的人文危机起源于伽利略和笛卡尔,在这个时间点上,世界开始被割裂成两个部分,一边是生活世界,是我们在前科学和科学之外的生活中经验到诸多事物所构成的时间世界,它不仅仅是感性的可知觉对象所构成的世界,而且是或多或少有价值的对象、美丽的对象、危险的对象所构成的世界。另一边是理论科学的世界,它是我们对这个丰富的、可直接的世界进行抽象,剥去所有价值以及与我们的情感生活相关的其他部分,诸如颜色、气味、温暖、安全等感性的性质,将具体的生活排除在视线之外,将世界缩减成科学与数学探索的一个简单对象,能够被理性和概念描述、掌控、推理、研究的对象。
在《看不见的城市》几段对话里,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化身成双方的代表,一个是抽象化的、纯粹理性的、铺天盖地而来的、让世界臣服的概念思维;另一个是专注的、兴味盎然的,把目光聚焦到经验的、记性的、眼前一棵树的、一片林子的...实体思维。
忽必烈汗看着他面前的棋盘,想着他的帝国,以及这一切的意义,他困惑了。
可汗努力全心沉浸于棋局:但现在他却忘记了为什么下棋。每一局无论胜负都有一种结局,可是赢的或输是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风险是什么?终局擒王时,胜方拿到了国王,棋盘上余上的就是黑白两色的方格子,此外什么也没有。通过把自己的胜利进行支解,使之还原为本质,忽必烈便得到了最极端的运算:帝国国库里的奇珍异宝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被化约为棋盘上的一块方格:虚无......。
屏蔽对生活世界的感知,探求存在的意义,就像伊卡洛斯独傲的飞向太阳,很容易被烤化蜡做的翅膀,被单一的理性宿命式的引向虚无的绝境。在这最让人绝望的一幕,马可·波罗说出全篇最为动人的话:
陛下,您的棋盘是用乌檀和槭木两种木料镶嵌而成,您的慧眼望着的那个方格是从旱年生长的树干砍下来的,您看清它的纹理了吗?这儿有个小节疤。早春时那儿有个幼芽冒出来,但被夜
间一场霜给打坏了。
图片转载至 Seeing Calvi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