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侯孝賢的現代經典《悲情城市》以及林正盛的《天馬茶房》中再探二二八事件,他們使用兩種非常不同的表述。從外緣到中心、從寂靜到言說、從歷史折射到歷史反思,侯孝賢和林正盛為悲痛的歷史記憶提供了兩個種強烈的影像。
文:白睿文(Michael Berry)
儘管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造成難以抹滅的傷痕,並持續在學術和政治領域中,引起激烈的反應和高度的爭議,但迄今只有兩部劇情片在大眾文化的背景下,試圖重建並重現這個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悲劇。相隔十年的創作,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和林正盛的《天馬茶房》(1999)用了非常不一樣的呈現策略。前者利用距離和沉思的觀察,後者則回到事件發生之地,重新思索當時二二八這個歷史夢魘開始的實際片刻。在這個章節,我提供了這兩部電影的閱讀素材,並探索、重新想像這個台灣近代的重要事件如何被搬上大銀幕。
儘管只有兩部劇情片電影直接處理二二八事件,但這個事件對台灣當代電影有著令人感到迷惑、深奧的影響作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標示了恐怖事件的開始,也是四十年戒嚴和白色恐怖期間,政治壓迫的開端。儘管在本研究的範疇之外,於白色恐怖的煙幕下,一些不斷增加的有關國家暴力的電影也應視為二二八悲慘事件的延伸。
這類電影包括楊德昌一九九一年長達四小時的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及王重政和洪維健二○○一年的敘事詩作品《天公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主要描述少年小四的父親面對掌權者持續不斷的審問和迫害,以及小四和他中學同學的生活。《天公金》則追蹤受國民黨政權壓迫數十年後的後遺症,以「歷史的傷痕可以被原諒,但是永遠無法忘記」的墓誌銘作為結論。
然而,台灣白色恐怖電影的分水嶺是一九九五年徐小明的《去年冬天》和新台灣電影先鋒萬仁的《超級大國民》首映時。《去年冬天》改編自作家冬年同名的小說,是有關美麗島事件受害者的故事。此事件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爭取民主示威遊行失敗之後。《超級大國民》探索一位前政治犯所面對的罪與罰。許毅生因為參加「政治讀書會」而被監禁,無意間洩漏對於他的朋友陳政一有害的訊息,導致陳政一被判死刑。在被關了十六年以及超過十年在養老院的自我隔離之後,許毅生開始以旅行來對抗過去,並尋找他老朋友陳政一的墳墓以慰內心的愧疚。
同年評價很高的白色恐怖電影是侯孝賢的《好男好女》——侯孝賢三部曲的最後一章。伊能靜扮演女主角。這部電影是侯孝賢結構最複雜的電影之一,從三個不同年代不同的故事切入,沉思如何再創造台灣的過去。
上述這些電影全都出現在一九九五年台灣第一次全面民主選舉的幾個月前,並非巧合。在那有著激昂的政治辯論和主張的時代,過去的事件如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呈現了一種新的意義,它們不僅僅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操作選票和提供選舉議程的政治手段 。這是最悲慘的諷刺——在五十年的政治迫害之後,受到不公義的政治議題所加害的受害者,現在又成為另一個議題的受害者。這種將過去不公義的創傷,使用在建構一個新國家和國家主義觀點的方式,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在一個「無法言喻」的悲情城市訴說痛苦
三十幾年來,侯孝賢詮釋並重新定義台灣的電影。八○年代早期,他初期的經典作品如《童年往事》、《戀戀風塵》,使他在台灣新電影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了八○年代晚期九○年代初,他的劃時代作品「台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及至《海上花》、《千禧曼波》和《最好的時光》等作品,侯孝賢不斷地呈現與眾不同、具影響力的電影視野。
他擅長使用長鏡頭、強烈的寫實主義,展現對台灣歷史的熱情、淡漠的渴望,有距離感的熱情是他作品的特色,觀眾彷彿看見想像的過去。加上經常合作的核心工作人員,如編劇家朱天文、剪輯廖慶松、音效設計杜篤之、電影攝影師李屏賓以及演員高捷,侯孝賢開創了台灣電影的新標準,影響了新一代的本土導演,包括徐小明和張作驥等。
一九八九年侯孝賢的三三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和年代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合作的電影《悲情城市》,是他最具抱負的影片,也是稍後被稱為「台灣三部曲」的第一部曲。促使這部影片具有開創性的原因有:它是台灣第一部以同步錄音方式拍攝的電影,片長一百五十八分鐘是他製作最長的影片,它也是台灣第一部在重要國際電影節中獲得首獎的影片——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最佳影片獎。然而這部電影真正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它描繪了政治敏感和爭議不斷的二二八事件。《悲情城市》是台灣解嚴不到兩年所發行的第一部處理一九四七年暴行並備受爭議的電影。
影片受爭議的部分包括:這部電影在柏林獲得國際獎項的殊榮、一九八九年在台灣無法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的意外 、侯孝賢對女人的描繪和他有關政治的歷史表述(更確切的說,不表述)。然而,爭論的焦點在於侯孝賢對二二八事件的表述。《悲情城市》曾經是禁忌的歷史背景,將這部電影提升到幾乎是神話的境界。關於八○年代晚期台灣的文化事件,此片的發行有很深刻的歷史、社會和政治意涵。
回想電影的源起,侯孝賢提到:
台灣新電影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拍自己的成長背景、台灣經驗。這部分主題表現在電影上,比小說晚了十年。《悲情城市》所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一直是個禁忌,所以更晚,一九八九年,整整晚了十年。隨著蔣經國(1910-1988)去世,戒嚴解除,時代變了。空間打開了,用電影討論這個主題成為可能。即使在戒嚴之前,我也聽說很多過去的故事、看了很多跟政治相關的小說。比如說陳映真 。這引發了我的興趣而開始去找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資料。這是個時機,我本來不是想拍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下一代人的生活;他們活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之下。後來正好解嚴,我感覺這時來拍《悲情城市》是一個時機。(白睿文,2007:223)
《悲情城市》主旨並非描繪那些生活在二二八陰影底下的人們,實際上影片沒有正視或聚焦於事件本身。相反的,影片以更複雜的手法追溯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間,裕仁天皇投降和台灣光復,而共產黨占據大陸,台灣被轉變為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堡壘等歷史事件。《悲情城市》是五年歷史空窗期、文化轉變和衝突的一個電影沉思,當中存在著一九四七年二月的悲慘事件 。
影片主要的情節圍繞在林阿祿(李天祿飾)一家,年老的家長也是地方角頭的林阿祿和他的兒子們:林文雄(長子,陳松勇 飾),在當地經營「小上海酒家」;林文良(三子,高捷飾),從中國大陸的戰爭中歸來,心智受損,並患有砲彈休克症(長期作戰引起的精神疾病);林文清(么子,梁朝偉飾),聾啞攝影師,在小鎮附近經營一家照相館;次子林文森,當地的醫生,擔任軍醫,在亞洲日本戰爭中生死未卜。《悲情城市》見證五○年代晚期,在不斷變化的台灣政治情勢之下,努力生活但終歸式微並瓦解的一個大家庭。最後毫髮無傷的是——年老體衰而無助的大家長林阿祿。
電影片名已經指出這個豐富且具挑戰性作品的複雜度。在《悲情城市》中提到的「城市」有許多意涵,包括九份,這個小巧風景如畫的礦城,林文清在這裡經營的照相館,也是許多場景的拍攝地點,港口小鎮八斗子則是林家居住的地方。兩個地方在空間上似乎都符合「悲情」的特質。然而,真正事發的「城市」——台北——卻在銀幕之外,一個看不到悲情和暴力的地點。那裡是陳儀廣播有關暴動、事件的起源,也是暴力浪濤擴展之地,陳儀的廣播片段被安排緩緩進入影片的敘述。
電影上映的日期剛好是天安門屠殺之後的幾個月,許多觀眾諷刺地將這個城市比喻為北京,儘管《悲情城市》完成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 。當被問到這個片名的意義時,侯孝賢提供了不一樣的解讀:「《悲情城市》其實是講台灣的意思。這原本是一首台語老歌(〈悲情城市〉),也是另外一部台語片的片名,叫做《悲情城市》 。不過它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是一部講愛情的片子。」(白睿文,223)
在這裡,一九四七年的台北的時空型(chronotope),充滿暴力和不安,此種氣氛不僅蔓延到九份和八斗子,也蔓延到整個台灣島——在二月和三月初事件在台北發生時,便很快地擴大並蔓延到幾乎每個主要城市。侯孝賢的談話暗示這部影片寓意的力量,遠遠超過林家成員個人所承受的悲劇 。
更廣泛地來說,這部電影試圖說出歷史的苦難(historical pathos)和難以言喻的痛苦,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經過四十年的沉默之後,《悲情城市》帶來了對澄清、正義和結束對立的期待。這部電影試圖表現言語無法表達的——文化被壓抑、錯置和切斷的經驗,以及歷史碎裂、暴力和痛苦的重負。
電影前半部,有一個在當地一間醫院發生的場景(其中一個主場景具有象徵意義),一群醫院員工正在上普通話的課程,為了準備治療中國大陸來的病人。同樣地,普通話速成課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間相當普遍,在那段時間,台灣湧入大量的外省人移民和難民。課程本身暗示台灣語言、文化,甚至是政治領域的改變。然而,同等重要的是實際上說出來的話:
頭痛,
肚子痛,
你哪裡痛啊?(《悲情城市》)
明顯的諷刺是:在可能造成殘酷鎮壓台灣人民的行動前夕,一群醫生和護士(極具象徵性)說著台灣國語——解放者亦是壓迫者的語言,以了解(診斷其痛苦)他們未來的脅迫者的病痛。然而,諷刺之外是悲情,「你哪裡痛啊?」這個問題或許正是侯孝賢和他的合作者想通過電影語言探索的問題。《悲情城市》試圖為肉體、國家和二二八歷史的痛苦,以及為日本殖民後,回歸中國的政權轉移創傷發聲。然而,當這些醫生說著外來語,以診斷遠從大陸來的移民,侯孝賢應用新的電影語言,以一個明顯可見的詞彙和句法,希望喚起那些被壓抑的、無法言說的暴力。
沉默和暴力的展現,由林家第四個兒子的演技熟練地表現出來。四子林文清由香港著名演員梁朝偉飾演。因為梁朝偉不會說台語,林文清的角色被改寫,這個角色被改為聾啞人 。如此原本以為會限制了創造性的部分反而成了最有力的觀點;文清的聾啞有著高度的象徵意義。當侯孝賢說出:「其實創作一定要限制,創作沒有限制,等於完全沒有邊界,沒有出發點。你一定要清楚限制,知道你的限制在哪裡,它們成了你的有利條件。你可以發揮想像力,在限制的範圍內去發揮。」(白睿文,221)在《悲情城市》中,林文清的寂靜世界「說出」二二八事件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未寫於官方歷史中的方式,也道出不可能重新真實建構那事件,以及找回已經失去的全部 。
這個時候,視覺的焦點從圍繞桌旁的男人,轉到鄰近房間的吳寬美(辛樹芬飾)和文清。老師間的對話持續著:「準備好你的筆,到時候,你就是見證!」在此,使用見證這個詞,來「見」和「證」,意指「看見」或「證明」,這也是在南京大屠殺修辭中的一個關鍵詞。影片中的見證歷史,見證者的重要地位給了老何(何永康),一位大陸記者,由著名作家、文化人張大春客串演出的老何是重覆出現的角色,也是在整部電影中唯一從頭到尾說普通話的人。由於他是台灣知識分子中的大陸人,因此有獨特、客觀(或至少是有距離)的歷史觀點。然而,就如有人半開玩笑地把老何封為歷史的見證者兼記錄人,侯孝賢偷偷地把此榮耀歸予另一人。
在實施戒嚴的嚴格媒體審查下,老何的筆幾乎是無用的。反之,鏡頭轉移到林文清,他背對鏡頭幫吳寬美放唱片。當他轉身面對鏡頭,我們聽到隔壁房間最後的對話:「來,來,敬見證!」
這裡,諷刺地,林文清在視覺上被擺在真正見證者的位置——但是身為聾啞人,他能做的只有「見」,也就是看見歷史的暴行,卻無能「證」,證明或將鎖在眼睛後面的祕密傳送出去。電影倒數第二個場景,當他和家人決定放棄一切而逃跑之時,文清設定好相機和他的妻兒拍了張全家福。他唯一的安慰不是記錄歷史或是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混亂事件,而是保存他家庭的最後印痕。這個描寫和電影剛開始時,林氏家族在小上海酒家外所拍攝的團體照成了對比。一切只剩小小的核心家庭,但甚至這般的小家庭也無法倖存。下一個場景,文清被逮捕了。

林文清無法完成他見證歷史的重任,就如同《悲情城市》無法重演二二八事件一樣。然而,這可能正是林文清的生活和這部電影實際上的情況——歷史記憶的破碎和呈現的限制。在《悲情城市》中,痛苦、暴行和悲傷,藉由不表述(nonrepresentation)和沉默的政治緩和下來。
評論家對於電影中女性角色無法參與或重述歷史有許多意見。如貝雷妮絲.雷諾(Berenice Reynaud)和其他評論者所指出的,儘管電影的觀點由林文清、阿雪和吳寬美共同敘述,但後兩者是附屬的聲音,影片主要表達的是男性角色的經驗 。女性角色的無聲,或許在二二八事件後續鎮壓的場景中,可以清楚看見,阿雪和寬美正在討論其中一個受害者:
吳寬美:你們店什麼時候關的?
阿雪:三月啊!有一陣子是不是很亂?還死了很多人,隔壁也常被抄。
阿爸的朋友許先生也被抓了⋯⋯
吳母:阿雪!
這是唯一女性角色描述和二二八事件有關的例子。然而,正當阿雪要開口敘述時就被切斷了。文清的靜默是天生的,而且由於他的殘缺無可改變,但是阿雪和寬美的靜默是被迫的——由社會加諸其身。阿雪正處於打破禁忌的邊緣,藉由母系家長的角色被擺到適當的位置。她述說歷史的權利被否決,而許先生的命運永遠成謎,就如許多被國民黨迫害的受害者一般 。
關於林家的家世和家庭成員的生離死別故事,《悲情城市》好像有意不給觀眾提供一個全面的敘述。相反的,電影編織了一條複雜的繡帷,此繡帷由許多角色的展演、嘈雜繁複的語言、字幕、倒序和跳躍的敘述組成。敘述間的缺口、歷史管制的時刻證實是最有力的傳遞痛苦的方式。導演應用同樣的手法來呈現暴力,通常是間接的方式,或在鏡頭外發生、暗示、朦朧不清,或是以遠方觀點來拍攝。
侯孝賢利用長鏡頭、長距離拍攝展現暴力美學,將一些最殘酷的電影片段冷處理,《悲情城市》尤其明顯。雖然在他的其他影片中,如《南國再見,南國》暴力占了相當重要的部分,但侯孝賢在這部電影中呈現的暴力是經過沉思的,它超越身體,指向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普遍性的暴行。
侯孝賢的暴力美學和不表述策略結合,形成一種距離、沉默和空無所構成的視覺詩歌。由電影主要場景避開台北(以及任何和起義有關的城市),選擇九份和八斗子兩個大致上和二二八事件沒有直接關聯的地方可以證明。然而,當暴力不知不覺進入電影敘述時,又常常被以遠距觀察——或完全忽視來處理,這可以拿前述剛開始的一個場景為例,那時候文清只是象徵性地成為見證者。影片中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直接具體提到外省人與台灣人的衝突,事實上也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先兆:
「那天基隆警察打死一個賣菸的,你有沒有聽說?」
「有啊!有聽說,還聽說場面很激動。」
「是啊!聽說整個街道很激昂。」
「當然激動,差點出事情。」
「那些菸哪來的?」
「還不是那些大官走私進來的,紅包一塞,再多也進來。」
「虎不打,打一些蒼蠅蚊子幹嘛⋯⋯」(《悲情城市》)
這些描述和細節聽起來令人驚訝,它和二二八事件極為相似,但實際上它所指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發生在基隆的一件鮮為人知的事件——一個年輕男孩因為販賣私菸而被打死。這個殺人事件在當地引發小暴動,但是沒有兇手因此被捕。吳寬榮和其他知識分子的討論是影片表示預兆的設計,預示當時大陸人和台灣人之間,特別是地方香菸小販和公賣局查緝員之間的衝突。
電影中有一段有趣的呈現,是當基隆死亡事件開始被討論時,一開始鏡頭並不是放到知識分子的身上,而是寧靜的群山景色。在《悲情城市》中,不僅僅是暴力,甚至是暴力的討論也在空間上被其他景物所取代。正如基隆事件預示了二二八事件將在二個半月後於台北發生,這種視覺上的取代,營造了電影的策略,藉此暴力在電影敘述中,被折射並轉移位置。
其中一個令人瞠目結舌、運用取代手法的例子是驕傲、桀驁不馴的大兒子林文雄之死,他的生命落在一群上海黑幫人的手中,諷刺的是,他的死因不是國民黨二二八事件後續鎮壓台灣本土菁英的結果,而是牽涉到反對他的家人介入毒品交易。侯孝賢似乎提醒我們,在動亂的年代中暴力的動態和複雜性——衝突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二二八討論諸多刻板的二分法,其實在某方面來說,只不過是複雜的文化情境的現象。林文雄被殺害的殘暴鏡頭,有技巧地轉切入台灣美麗的山景,孤鳥飛過的鏡頭。鏡頭如此切入有其更崇高的意涵,藉此提供觀眾一個沉思及哀悼的空間,以反思他們所目擊的暴力。
其他取代暴力鏡頭的例子,包括林文清在監獄時的幾個場景。與他同牢房的人被警衛叫出去,幾分鐘後,文清以憂鬱呆滯的眼神注視著牢房外面,我們聽到砰砰的來福槍聲,表示牢友已被槍決。看不見暴力——只聽到,甚至觀眾知道那些聲音文清也聽不見。當文清最後被釋放,他拜訪已故牢友的家人,轉達一封寫著「你們要尊嚴地活著,父親無罪」的血書——他生命最後的遺物以及對噤聲暴行的最後見證。
影片中最暴力的時刻——唯一直接描述二二八事件的連續鏡頭——是一群台灣人在鐵道旁追趕並且毆打大陸人。三個台灣人不斷地用棍棒擊打一個已經倒下、沒有能力反抗的男人,但是這個暴力行為因為距離(以長鏡頭呈現),以及空間(受害者躺在地上被其他物體遮住)而變得模糊。甚至更多時候,影片以記憶的方式訴說暴力使其模糊;這是五、六個倒敘鏡頭之一,在文清向寬美講述暴力的時候。不管這些短暫的暴力影像是客觀描述「所發生的事件」,文清記憶的視覺呈現,或是寬美閱讀文清的便條時所投射的想像,都沒有呈現在觀眾面前。
在電影後半部,吳寬榮被捕、處死,以及最後文清被逮捕的情節都沒有直接描繪。《悲情城市》沒有直接呈現暴力,而是在銀幕之外,一個更大的歷史畫布上呈現,藉由暗示的方式更顯其殘忍和不安。這樣安排也反映出文清的無法言說,以及其所表示的歷史沉默。《悲情城市》是一部具挑戰性的電影,因為它有非直線性的結構、語言多樣性、文化複雜性、角色多元性,最重要的是,其歷史複雜性。這部電影使用距離來看過去的黑暗和靜默,表現無法言說的痛苦。

在二月悲傷陰影下的幸福進行曲
在《悲情城市》爭議性的初次上演之後將近十年,以三部紀錄片起家的導演林正盛,在他的第四部劇情片——一九九九年的《天馬茶房》(英文片名為March of Happiness《幸福進行曲》)——決定重提二二八事件。如果說,侯孝賢所拍的台灣史詩影片造成空前的商業成功,而且似乎在整個九○年代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仍然滿足不了民眾探知的欲望,令人好奇的是,這個事件並沒有激發其他的電影表述。這和繼侯孝賢之後,畏懼爭議或憂慮受到影響比較沒有關係,而和九○年代當地台灣電影觀眾流失,受到好萊塢和香港電影的影響較有關係(日本和韓國影響程度較小)。
林正盛籌拍遲來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第二部電影,事實上,他很早就播下種子並歸功於《悲情城市》不尋常的初次上映。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林正盛和他當時的妻子柯淑卿只拍過一部八釐米的作品。他們離開都市退隱山林,到台灣的梨山經營果園。在那段期間,這對夫妻得知他們喜歡的一個導演正籌拍一部令人興奮的新劇情片。這個導演就是侯孝賢,這部電影便是《悲情城市》,林正盛決定下山應徵工作。
他與《悲情城市》助理導演黃健和初次會面後,每件事情似乎都得到妥切的安排,柯淑卿負責分景劇本,林正盛當攝影助理。雖然最後他們無法成為片中一角,但林正盛和柯淑卿已經開始探索創作屬於他們自己的二二八電影,到最後,他們採用和侯孝賢完全不一樣的電影手法來呈現歷史。將近十年後,林正盛和柯淑卿最後終於有機會重提二二八,並且在過程中將「悲情」轉變成「幸福」 。
《天馬茶房》的歷史背景跨距大約兩年,從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起義的那一天。這個架構創造出的悲劇氣氛,逐漸展現朝向命運決定的那一天。它和一九三七年葉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的書寫策略極為相似,故事也是在暴力發生的那一天結束。《天馬茶房》成為二月起義的電影前傳,和《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一樣,實際上是一個愛情故事。
電影由《戲夢人生》和《好男好女》的演員兼音樂家林強主演,他扮演歌手/作曲家阿進。阿進是一個年輕浪漫、揹著吉他到處跑的理想主義者,活躍於一九四○年代的新劇場運動。一九四五年,阿進喜歡上同劇團的一個成員阿玉(蕭淑慎飾),她是當地魚丸之王的海龍王之女。海龍王試著安排他女兒和謝仁昌結婚,仁昌是一位有地位的醫生之子。這部電影描述這對戀人的磨練和苦難,他們努力克服傳統社會習俗,並且逃離阿玉被安排的婚姻。這些事件以日本投降為歷史背景,當日本人撤退,新的緊張局勢隨著國民黨而到來,在二二八事件時達到最高峰。
電影中重要的次情節是新劇團,阿進和阿玉都是此表演團體的成員。這個團體及其政治傾向、戲目的選擇、表演美學和所面對的壓力反映,回應了四○年代晚期台灣社會政局的快速變遷。從面對殖民壓力演出日本化的作品到慶祝這個島嶼領土「回歸」中國的演出,以及國民黨對於未使用國語表演的檢查制度。這個劇團的命運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命運,從對日本的屈從到戰後的慶祝,最後對於國民黨執政日益增強的不滿。
詹天馬,劇團中的一個成員也是主要的贊助者,在大部分核心劇情中扮演關鍵角色——儘管通常是在幕後。詹天馬(戴立忍飾)出現在舞台前和幕後,引導新劇團求生、轉變和面對命運。詹天馬身為文化聯繫者,負責引導並與日本社會高層和國民黨軍隊官僚體系溝通,贏得執政官員對團體的支持,且保護他們的創作自由,也使得他們的演出免於被檢查制度和文化霸權所影響,他完成了各樣任務。
詹天馬的角色是該電影結構的黏著劑,他將不同電影元素黏貼在一起。在許多方面,他讓觀眾想起崑曲《桃花扇》的楊文聰這個角色,楊文聰是劇中的畫家兼詩人兼官員,他籠絡各方,把劇中的角色和情節聯繫在一起,即使詹天馬缺乏楊文聰的虛偽。詹天馬把這部電影的主場景帶出,主場景就是他所經營的茶坊,以他的名字命名:天馬茶房。
在四○年代晚期,它是台灣社會各種獨特人物的聚集地,日本知識分子和間諜、台灣藝術家和革命者,甚至是國民黨軍官和地方菸商小販。茶房的密室加蓋兼做新劇團的總部和預演的場地,而前面的公共區域則為革命者和戀愛者共存的場地,一切在奉茶間進行。那是詩人和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是阿進和阿玉相戀的地方,是謝仁昌努力贏得阿玉芳心失敗的地方⋯⋯茶房同時也是一個以前日本顧客懷舊的地方,在被遣送回日本之前,他再度造訪,但此次造訪竟釀成悲劇,當他來到此地和壞脾氣的國民黨官員發生衝突時,悲劇發生了。藉由中日戰爭所殘留的暴行,國民黨官員冷血無情的殺害了前來懷舊的日本人。
林正盛利用發生在茶房周遭和其顧客間的社會、文化、經濟甚至語言的改變來反映台灣社會的縮影,傳達了四○年代晚期台灣社會戲劇化的轉變。他心懷悲憫傳達這個重新設計的社會結構,表現其複雜、豐富和悲傷——儘管無不誇大情節。但是,林正盛這部有如史詩和歷史油畫般的電影比起他們表面所呈現的更加複雜。天馬茶房不只是電影的中心場景,也是二十世紀台灣史上的重要地點。
真正的天馬茶房(參考之前賴澤涵、馬若孟和魏萼引用的天馬茶房),就是來自台北市公賣局的六位緝查員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會聚、調查線報販賣走私香菸的地方。因為他們發現一個可疑的四十歲小販,販賣非法的香菸。衝突在他們沒收小販的商品之後接踵而來,因此釀成悲劇,這也是揭開四○年來政治迫害的序幕。
電影名稱《天馬茶房》,主要強調這間茶房在空間上的重要性,標示了重提這個恐怖事件實體地點的象徵性,人民在此受到的傷害,將深深烙印在現代台灣史上。這部電影加上了匿名和無名的虛構聲音和身分,他們是一九四七年二月最後幾天,在天馬茶房周遭處於政治、文化、歷史和命運衝撞下的歷史人影,也是被形塑出來的人物。不像《悲情城市》採用空間和現實的距離主導沉思的觀點,《天馬茶房》透過以時間為主題的虛構空間重建事件,直接翻尋歷史的創傷。
儘管林正盛嘗試面對過去往前看,他與「歷史的對峙」(confrontation with history)經由想像斡旋,到最後他所創造出來的一九四七年的台北的虛構成分與歷史成分一樣重要。在影片中意外發生的主要事件,由日期的描寫可明顯看出,與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發生的實際時間點是不一致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林江邁和公賣局官員之間所發生的歷史衝突,在影片中被挪移到二月二十八日,無疑加深了這個特定日子的強度。)
影片中,海龍王同樣也選擇有重大影響的二月同一天,舉行他女兒和醫生之子的訂婚和結婚儀式 。阿進和阿玉同樣也在二月二十八日計畫一起逃離。他們不是逃往南台灣或日本,而是在「解放」的那一晚逃往「祖國」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的介紹也成為左派人士對於二二八所做詮釋的微妙參考——把起義視為由中國共產黨幕後操縱的無產階級革命。阿進是一位好演員,在台灣的舞台上他是浪漫的愛國者。阿進原來的情人是一位間諜,在替日本政府赴上海進行某次任務的時候被殺。阿進是她的靠山(或許也算是共犯?),她是一個年輕共產黨員,回到「家鄉」參與建立一個新國家。然而,阿進並未能實現他的夢想。
暴躁的國民黨官員草率處決在茶房碰見的一個日本人,在此預示了阿進之死。同樣是這個官員,在一陣憤怒和絕望之後,從舞台上開了一槍示警,殺死了在椽上的阿進。阿進死了卻如同生前,在舞台上為他的國家做最後的犧牲。這時候,阿玉在碼頭等待著要逃往大陸,遇到了阿進的鬼魂。他的魂魄歸來,代表這對戀人遲來的重逢,以及歷史幽魂的再度出現,在幾十年的沉寂之後,歷史幽魂藉著影像重現 。
在侯孝賢的現代經典《悲情城市》以及林正盛的《天馬茶房》中再探二二八事件,他們使用兩種非常不同的表述。從外緣到中心、從寂靜到言說、從歷史折射到歷史反思,侯孝賢和林正盛為悲痛的歷史記憶提供了兩個種強烈的影像。兩部電影之間一道最後的連結與不同之處,在於舞台的使用。舞台劇——本身是表述和重現歷史有力的隱喻——在兩部電影都具高度的象徵和影響力。
之前提到的《悲情城市》中「羅蕾萊」那一幕,文清將小時候鍾愛傳統戲曲的動人回憶轉述給寬美聽。從樹上摔下使他變成又聾又啞,也結束了舞台上一個生命的希望。當然,後來他將對於戲劇的喜愛,投入另一種藝術形式——攝影。但是在《悲情城市》中的(歷史)舞台是封閉的,表述成為角色無法可及之事。除了瞬間回顧孩童在教室模仿戲曲演員,在戶外演出場地玩耍,傳承歷史的舞台並沒有出現,它已經被破壞了。
《天馬茶房》採取另一種手法,舞台在中央,既是實體也是象徵。電影以兩個舞台表演為中心,情節隨之開啟和關閉,主要的角色都是與《天馬茶房》有關的劇團演員——天馬茶房就是最初暴力發生之地。這部電影志在表述,甚至更有力的是《天馬茶房》為有關探究暴力的中心,各個角色在藝術上、生命中、舞台上、歷史上扮演深具挑戰性的雙重角色。最為明顯的是在電影尾聲,這個魯莽的國民軍官衝進戲院,殺害了理想主義的主角阿進。這個戲劇舞台變成歷史舞台。
在《悲情城市》從周遭重新想像歷史後的整整十年,《天馬茶房》把這樣的歷史搬到舞台中心——實際且象徵。然而,從侯孝賢距離策略的運用到林正盛之急於表露,因此有些東西被遺落了。林正盛強烈的敘述將歷史直接呈現(常以強迫方式將歷史搬上他的電影舞台),諷刺地無法達到《悲情城市》所造成的震撼。或許沉默之聲仍然為過去那些難以理解此事件的幽靈,提供了最終的見證。
書籍介紹
《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麥田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本書是美國加州大學漢學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歷經多年思索,針對華人世界從1930到1997將近七十年期間,發生在中國、台灣、香港的重要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歷史創傷」研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依照時間先後順序為:霧社事件(1930)、南京大屠殺(1937-1938)、二二八事件(194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天安門事件(1989)、香港回歸(1997)。
這些事件各自代表了華人暴力與暴行的重大意涵,作者從相關的文學、電影、攝影作品、流行文化入手,分析探討在這些作品中,暴力如何被想像、轉變和進化。從這些挑選出來的暴力事件中進一步研究、反思人類的野蠻和殘暴以及它所產生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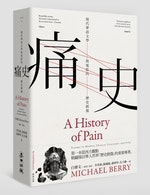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專題下則文章:
創傷與感覺創傷的方法: 二二八揮散不去的《痛史》
TNL 網路沙龍守則
TNL網路沙龍是關鍵評論網讓讀者能針對文章表達自身觀點的留言區。我們希望在這裡,大家可以理性的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對不同的論點保持開放心態,促進多元意見的交流與碰撞。
現在網路上的留言討論常淪為謾罵與攻擊的場域,反而造成了彼此更大的歧異,無法達成討論與溝通的目的。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我們希望打造一個讓大家安心發表言論、交流想法的環境,讓網路上的理性討論成為可能,藉由觀點的激盪碰撞,更加理解彼此的想法,同時也創造更有價值的公共討論,所以我們推出TNL網路沙龍這項服務。
我們希望參與討論的你謹記以下幾個基本守則,與關鍵評論網一起提升網路沙龍的品質:
- 尊重多元:分享多元觀點是關鍵評論網的初衷,沙龍鼓勵自由發言、發表合情合理的論點,也歡迎所有建議與指教。我們相信所有交流與對話,都是建立於尊重多元聲音的基礎之上,應以理性言論詳細闡述自己的想法,並對於相左的意見持友善態度,共同促進沙龍的良性互動。
- 謹慎發言:在TNL網路沙龍,除了言論自由之外,我們期待你對自己的所有發言抱持負責任的態度。在發表觀點或評論時,能夠盡量跟基於相關的資料來源,查證後再發言,善用網路的力量,創造高品質的討論環境。並且避免對於不同意見的攻擊、惡意謾罵言論。
為了鼓勵多元評論與觀點的碰撞激盪,並符合上述兩個守則前提下,我們要求所有沙龍參與者都遵守以下規範,當您按下同意開始使用本沙龍服務時,視為同意此規範:
- 您同意為您自身言論負完全法律責任,您不會發表不適當言論,包含但不限於惡意攻擊言論、歧視言論、誹謗言論、侵害他人權利或任何違法情事。
- 您同意您不會張貼任何帶有商業行銷或廣告直銷之勸誘式廣告內容。
- 本集團有權管理沙龍所有內容,以利維護沙龍良性的溝通環境與氛圍。
- 本集團有權隨時新增或修改此規範,如有增修將公告於本網站。若公告後您仍繼續使用本網站,即視為同意接受增修版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