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被一把死別的大刀單刀直入地插在心臟,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我不過從新竹搬回台北,老爸卻在一夜之間從人間直接搬到天國?
女兒六足歲,必須確定學籍,我們決定搬回台北定居。每個假日,奔馳於高速公路找房子,定期南下探望老爸的時間一延再延,我承諾再過十來天、父親節前後一定回去,電話那端傳來不忍為難子女卻又藏不住失望的聲息。
十五歲離家,最久不逾三個月回家一趟已成潛規則──感覺那是能忍受的思念張力極限,二十幾年始終不變。但這次,我已破壞規則,思念常似被吹脹的氣球,就快撐破胸腔與腦門;半年,對我來說,時間怎麼走的,何時走的,我渾然不知,但對老爸來說,一百八十幾個凝態的日子,時間老似黏膩的溼臭裹住全身、圍在周邊如如不動吧,真不知他是如何度過的?
老爸中風後,清晨由三哥背坐客廳沙發上,便是他的一日生活;原本撐持一個家的近六呎身軀,如今連起身擊斃在耳邊挑釁的蚊子的能力都無,每天坐望出去的、門框框住的灰白與半棵老榕,偶來的引擎運轉聲、機車聲、母親堂嫂嬸婆的作息聲影,就是生活風景的全部。
那段日子,遇週休我便想南下,但生活現實總將我們往北拉,拉離孩子超愛的動物園、十八尖山步道,拉往更車水馬龍的都會,早晚遊走繁華巷弄為覓一間房而汗如雨下、頭昏腦脹,只能在又接到老人的「搬厝哪會那尼久?」時盡力安撫一個孩童般的、不安的思念靈魂,然後責怪自己的食言、一再拖延。
敲定搬家日前兩週,我邊照顧孩子邊將分散在四十幾坪屋內五年了的家當分類、打包、裝箱,本來井然的物件被我搞得失了序、亂了碼,隱喻內心的兵荒馬亂,疏忽陽台上的眾盆栽也要喝水才能開花才能活。
搬家公司的人將零碎的袋子塞進家具交疊的縫隙,覆上塑膠布,將繩索纏在車斗四周的鐵鉤,外子開車載一雙子女,我蹬上搬家車的副駕駛座,出發了。兩旁風景往後飛拋,將娘家的距離愈拉愈大,但我已像童年在田裡勞動大半日後返家、管他身形狼狽地將背脊貼合在椅背上──終於貼近對老爸的承諾──冷氣孔送來的涼風中,摻雜些許輕鬆。
一個多小時後,搬家工人離去,我再度面對一屋子的毫無頭緒;忙亂中,父親節逼近,我加快手中動作;憔悴不堪,真想偷懶一下,但想到老爸,我硬撐下去。三四天過去,新家雛形大致底定,佳節氣氛點綴街景,躍然於生活週遭;我看著鏡中身影,雖質疑「這是我嗎?」,但心中有一股安定的力量──就快可以見到老爸了。
父親節前日。我陪兒子到幼稚園,辦好入園手續,為搬家任務畫下完整句點,步伐透現久違的輕盈,漫賞巷弄綠意間腦海浮現老爸見我走入三合院時的歡愉。然而,當我回到家門外,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已穿透門板聲聲喚,我猜想是兒子發現我又偷偷離開而嚎啕大哭,趕緊扭轉鑰匙,未料,當我接起,話筒那端傳來的不是兒子的哭聲,而是三哥的哽咽:「圓仔,爸歿去啊,你傳傳咧,緊轉來……」
記起那個清晨。城市還昏睡,我在醫院門口排隊等拿號碼牌,忽地,四五個人從計程車裡匆匆竄出,以跑百米之姿競奔院內。這時,有人說:「這是接到病危通知的,才會在這時候奔來。」而我,竟被一把死別的大刀單刀直入地插在心臟,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連急奔以見至親最後一面的機會都不可得?原來,我搬家的這些日子,老爸的生命也在準備搬家?花了半年時間,我不過從新竹搬回台北,老爸卻在一夜之間從人間直接搬到天國?
從學生時代的「遊街式搬家」,到婚前的「計程車式搬家」,再到養兒育女後得叫卡車才能完成的多次搬運裡,每次都辛苦。但這次,多了自責和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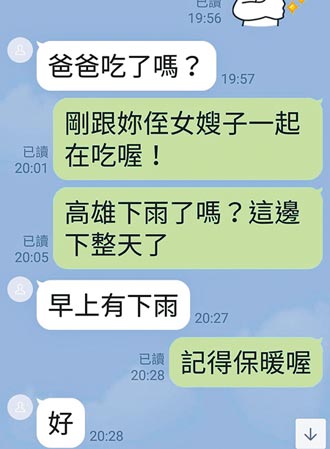






發表意見
中時新聞網對留言系統使用者發布的文字、圖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權利。當使用者使用本網站留言服務時,表示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規定:
違反上述規定者,中時新聞網有權刪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鎖帳號!請使用者在發言前,務必先閱讀留言板規則,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