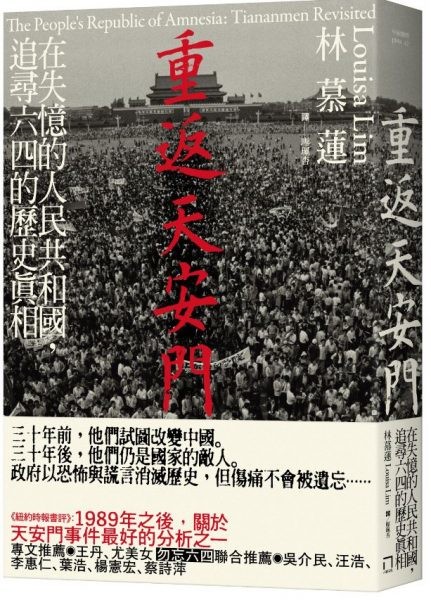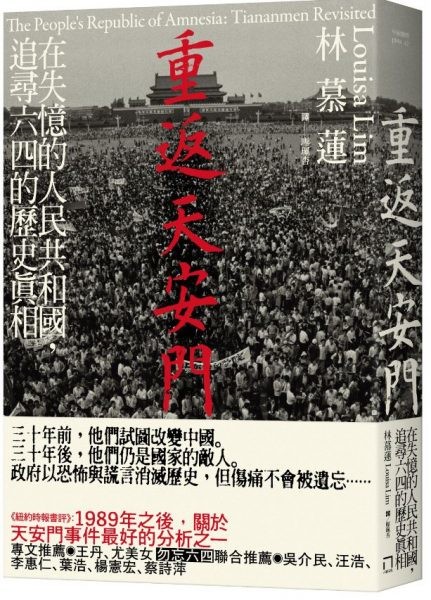【《BO》編輯檯好書推薦:《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你聽過吾爾開希,也好像聽過人家說他是騙子,沾著天安門事件的光逃出中國過活。故事的脈絡與真相,你能透過這本書找到。
>> 到博客來找這本書 六四天安門事件領袖之一吾爾開希,在事件最後、學生撤離之前就離開廣場,逃過了被中共坦克壓成肉餅的命運。
因為這事,他成為人人口中的社運騙子。
他是逃跑者,還是逃亡者?透過《重返天安門》這本的紀錄,由你得出你認同的答案吧。 (選書編輯:鄒家彥)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運動領袖之一,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現定居於台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文/林慕蓮
吾爾開希,來自共產主義信奉者家庭
吾爾開希自小就接觸政治,在十一歲的時候成了小紅衛兵。當時正值毛澤東十年混亂的文化大革命末期,小紅衛兵效仿他們的前輩行事,那些前輩的目標是「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
最初加入紅衛兵的都是大學生,他們以「破四舊」——破除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為目標,專門攻擊反革命分子,把他們的學院機構搞得天翻地覆。
身為一個小紅衛兵,吾爾開希在學校學習了抗議的藝術,他參加模擬成人政治活動的小版群眾集會,在集會上大喊口號,高唱革命歌曲,還煞費苦心抄寫批評鄧小平的海報。後來,吾爾開希變成少年先鋒隊員,頸上圍著象徵革命烈士鮮血的紅領巾,最後還加入了共青團。
跟一般學生領袖出身不同,他的父母是來自新疆突厥少數民族的維吾爾族,新疆邊界與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其他國家接壤。不像大多數維吾爾人那樣信奉伊斯蘭教,兩人都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
吾爾開希的父親曾是一名四處奔波的牧牛人,十四歲的時候被優先送去北京接受教育。吾爾開希的童年時期,他父親的工作就是將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書籍翻譯成維吾爾語。文革期間,當兒子在學校製造政治混亂的時候,父親則幾乎被批鬥到要自殺的地步。儘管如此,他父親仍繼續在國營出版社工作,直到兒子參與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活動,才中止了他的晉升機會。
吾爾開希的母親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工作,他們一家就和其他「維吾爾出版人」一起住在「新疆區」。自小,吾爾開希就極為崇拜軍人——那時,每個小男孩的夢想都是成為士兵。他最喜歡的遊戲就是穿上一件小版海軍制服,頭戴一頂繡著金錨的帽子。他最好的朋友伊爾奇姆(Erkhim)與伊利夏提(Ilshat)也會穿上兒童版的陸軍和空軍軍服,三個小兄弟就一起玩打仗遊戲。
不過當時北京一直有輕微的種族歧視狀況,吾爾開希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父母出乎意料地決定要搬回新疆省會烏魯木齊。吾爾開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熱忱,隨著當地出版的一份野心勃勃的學生報紙一起激發出來。當報紙發行到第三期的時候,已經賣到校園外了。
吾爾開希成為「出頭鳥」的開始
吾爾開希尖刻的社論最受矚目,而且越寫越發大膽,最後還在一篇文章斥責一名粗魯的老師不僅毆打學生,還閱讀他們的信件。這份報紙的名字叫《出頭鳥》——出自中國諺語「槍打出頭鳥」,比喻出頭的人容易成為被打擊的目標。事實上,刊登吾爾開希批評老師之文章的第三期,成了該報的最後一期。至於吾爾開希這隻出頭鳥呢,則是立即被開除學籍。
到了下一個學校,吾爾開希對政治的介入又更上一層樓了。他遊說學校允許學生兼職打工,然後再說服這些學生將他們部分的薪水捐給當地一家孤兒院。他在參觀一間孤兒院時,被其年久失修的慘況嚇到了,於是他寫了投訴信給省的最高官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黨書記。
這件事驚動了高層,吾爾開希被共青團團長召見警告。然而那個時候,大學入學考試正迫在眉梢,所以吾爾開希改變策略,轉而將全部精力投注在準備考試上。他設計了一套讀書方法,每晚只睡五小時,分三個學習時段,盡量擠出時間來念書。如此的辛勤努力得到了回報,他考上全國最好的教師培訓學院,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教育管理專業,這給了他回首都的車票。
當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無法上大學,吾爾開希就這樣變成了那百分之一的菁英。
光是被大學錄取,就能讓普通的青少年升格成「天之驕子」,讓他們鶴立雞群。註冊入學之後,吾爾開希發現,高年級的學長姐都認為大一新生很膚淺、唯利是圖、自私自利。他開玩笑地說,從前時候學生們被分成四類:迪斯可咖、麻將咖、賺錢咖,還有一類是打算出國留學的托福咖。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吾爾開希過著一生中最逍遙的時光,晚上出去玩、和女孩子約會、打工賺錢,在課業上就是打混過去。他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但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過世後,一切都變了。(《報橘》編按:胡耀邦,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具體執行者,但後來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1989 年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起大量的民眾懷念與抗議運動,運動的加劇最終導致六四事件。)
「那一刻,我們所有封閉的感官都甦醒了。一夜之間我們變得非常關心政治。」
吾爾開希是八九學運第一個站出來說話的學生
吾爾開希喜歡回憶他在運動早期時候的樣子,說自己簡直像個「將軍」一樣,在他的學生軍團面前相當有威信。他是最早出頭的學生領袖之一而聲名大噪,卻全然不知日後這將使他走上二十五年的流亡之路。
他在胡耀邦去世兩天後首次登台亮相,當時有數百名學生聚集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園裡,悼念這位已故的領導人。成群的年輕學子齊聚一堂,卻因為緊張焦慮而靜默無聲,誰都在等著別人第一個站出來說話。
對吾爾開希來說,往前踏出一步是一個瞬間的決定,不是出於什麼政治考量,而是因為他對這種集體怯弱感到厭惡。
「我不想做縮頭烏龜。」他回憶道。所以他站出來了,聲音又響亮又清晰。「我叫吾爾開希。我是北師大學教育管理學院八八級的學生。我住在三三九宿舍。」吾爾開希公開了他的個人資料,這不僅是公然藐視當局,他那帶有獨特維吾爾風的名字,還保證讓所有人從那刻起永遠記得。
一天後,他在張銘加入運動的同一場靜坐上,再次成了鎂光燈焦點。一如以往,吾爾開希又把自己推到最前面、最中心的位置,擔任起領導的角色。他自稱:「選學生領袖的時候,只有我站了出來。」吾爾開希站在學生群眾的最前面,要求所有學生寫下自己不敢大聲說出的想法。然後他再用幽默的實況評論方式,大聲朗讀那些寫下來的話,他的衝動性格和戲劇性一覽無遺。
在這場運動還在凝聚的早期階段,吾爾開希認為自己既是全劇導演又是製片人。靜坐持續了幾天之後,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發表了一份公報,呼籲發起罷課及一場學生集會。
他沒想過接下來會如何發展,所以當成千上萬名其他學校的學生在集會前開始湧入校園時,他感到相當吃驚。
政府也在緊盯局勢;在吾爾開希釘好他的第一張海報不到幾個小時,他父親就被從中央黨校給傳喚,還去受訓學習如何管教任性的兒子。他父親為尋找兒子,一整天從一個宿舍找到另一個宿舍去;而這個兒子也同樣在躲避父親,極力避免公然忤逆長輩的情節上演。
集會指定的時間到來,成千上萬的學生聚集在他的校園裡,吾爾開希幾乎走不過去。為了讓眾人能夠看到他的身影,他爬上了女子體操的高低槓上,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吾爾開希坐在最高的鐵桿上,雙腿踩在較低的桿子。他請志願者將手電筒的光打在他的臉上,充當照明。他還創造了一種「群眾傳聲筒」,請距離近的學生幫忙大聲複誦他的話給後排的學生群眾聽。
現場,估計有六萬名學生參加集會。從黑鴉鴉的人群裡射出的所有燈光,全都照在同一個人身上,形成了萬眾矚目的一刻。吾爾開希低頭往下看,正好看到自己的父親就站在面前。他的父親像是一夜之間老了好幾十歲。
葬禮上的司令員胡耀邦葬禮前夕,這群學生只有一個目的地。一間接著一間學校的學生走出大門遊行,隊伍排成五列,旁邊有擔任糾察隊的學生排成警戒線,他們其中一隻手臂上戴著紅袖章。
進入天安門廣場,學生跪求領導階層出來對話
一抵達天安門廣場,吾爾開希就命令學生們挽起手臂,一起穿越廣闊的場地,把廣場上的其他人都趕走。從這個臨時起意的舉動看得出來,學生們想要保持運動的純粹性,也許他們擔心,非學生人士的參與會使他們受到「黑手」滲透的指控。
當天晚上,他們在廣場上紮營露宿。翌日,四月二十二日,當中國領導高層聚集在人民大會堂裡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時,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向廣場。軍隊全程透過廣播向學生發送消息,場外的學生聽到胡耀邦的棺木繞過他們,從後門離去時,全都很憤怒。
大群學生聚集在大廳的台階下,在吾爾開希的帶領下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
等待總理出面的時間越拖越長,過程中周永軍等三位學生代表越過武裝警察在會堂前布的封鎖線,到台階上下跪懇求接見。那份七點請願書卷軸高高地舉在頭上,一副古代忠心耿耿的老百姓向皇帝求情的模樣。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這個極具政治象徵意義的時刻變得越來越荒謬。三個學生跪了半個小時,剛開始帶有一種反抗,最後變成了絕望。
一些學生開始哭了起來,因為他們越發感到被領導拋棄。看在吾爾開希眼裡,下跪是一種很封建的姿態,正是他所憎恨的溫順與軟弱。他告訴我:「我感覺我是在指揮一場戰鬥,但下跪不在我計畫之中。」學生人數遠遠超過士兵人數,他曾冀望能利用人數之眾來威嚇對方,然而事與願違。下跪,就代表把主動權讓給了關在大廳裡的共產黨領導人。
吾爾開希形容,他當時對此感到厭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指揮得動三千或者四千呼號的民眾。那不是我能做到的事!」他自封當晚行動的「司令員」,吾爾開希最後下令學生從廣場撤退,返回各自的學校。
隨著運動聲勢越來越大,到處都可見到吾爾開希的身影。學生們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時候,最初選定的代表人選被推翻,幾天內吾爾開希就成了主席。成立對話代表團時,他也是成員之一。他會見外國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確立了身為主要參與者的地位。
他還記得那些意氣風發的日子;當學生們聽到,他們呼籲對話的聲音獲得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附和時,他們覺得勢頭是站在他們這邊的,「甚至在大學裡,院長看到我,他跟我握手就像在跟未來的國家領導握手似的。我們要贏了。我們要取得戰鬥的勝利了。」
另一名也是很早就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生就是王丹,他戴著眼鏡,是很理智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他的「民主沙龍」曾邀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來學校講談。相較之下,吾爾開希則淡化了政治理論的地位。流亡後不久,他提及:「中國的搖滾樂對學生思想的影響,比那些年邁學者提出的任何民主理論都要大。」
台灣歌手侯德健的歌《龍的傳人》成了學生運動的主題曲,部分是因為這首歌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侯德健也曾和學生們一起露宿,還在六月四日時幫忙協商撤退離開廣場的事情。
天安門廣場一度成為侯德健及其他音樂家的搖滾音樂會舞台。侯德健在一部美國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表示,搖滾樂受到西方文化啟發,已經成為一種自由化的形式。「參加一個搖滾樂音樂會的時候,大家那種很瘋狂的感覺,完全是要求自我被解放,和表現自我的那種東西。」
吾爾開希的「神秘心臟病」和絕食創舉,吸引國外媒體報導中國年輕人的犧牲
我問吾爾開希絕食是誰出的主意,他用拇指指著自己的胸口說,「正是在下」。這個主意,是吾爾開希、王丹和其他四個朋友一起享用難以下嚥的炸黃瓜和牛肉的時候想到的。他們抱怨伙食太差的同時,絕食抗議的想法就冒出來了。這是蓄意升級運動的策略。當時由於學生開始抵制罷課,重返校園,運動的勢力漸漸消退。
五月十三日開始發動絕食抗議活動,不久後就看見身穿白衣的醫護人員在廣場上奔波,用擔架將暈倒的學生送往醫院。這一幕年輕人為國家未來犧牲自己的場景,震撼
了許多在此之前從未參與的人,吸引了一百多萬普通市民湧入廣場。
國際媒體也來採訪;學生為爭取自由和民主,發起對抗共產黨領導的抗爭運動很上鏡頭,這麼好的故事不報導是暴殄天物。加拿大記者黃明珍(Jan Wong)在她的自傳《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Red China Blues)中描述,她當場抓到一個絕食抗議人士背包裡藏有優格。當她提出質疑時,對方回答:「吃零食沒有問題。這不算真正的食物。」
黃明珍曾報導過優格的故事,但她也坦承自己從未真的講述過關於絕食抗議的完整事實。黃明珍寫道,「一開始就像個遊戲,學生們在指示下很誇張地昏倒,然後全世界的媒體就當他們是真的在挨餓。」 玩這個遊戲的翹楚就是吾爾開希,他在絕食過程中穿插了一場充滿戲劇效果的昏厥,自稱是因為罹患一種神秘的心臟病。他有自信到甚至還找了一位西方記者幫他作弊,並賭他的個人魅力能保護他不被抓包。
吾爾開希半夜捎訊息給美聯社記者潘文(John Pomfret),請他開車到外邊的市場幫他買食物。「我不能自己去買,」吾爾開希解釋,「如果被人看到,會對運動造成影響。」潘文在他的書《中國課》(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描寫了吾爾開希偷偷滿足口腹之慾的樣子,「吃完豬肉麵後,他又吃了雞絲麵、青椒和火腿麵,還有湯麵——他在我旁邊把所有食物都掃個精光。」
潘文在十六年後才寫出了吾爾開希的欺騙行為。當我向吾爾開希求證這是否屬實的時候,他停頓了很久。「他不應該寫出來,」他勉為其難地說,「這很不友好。」「但,那是真的嗎?」我追問。
又是好一陣子的停頓。然後他往椅背上靠,深深嘆了一口氣。「不予評論,」他說。整個人突然看起來累癱了。
不久之後,蘇聯總理兼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全世界媒體的注目下,到中國展開了標誌性的國是訪問,希望重新開啟與中國黨對黨的聯繫。媒體原本爭相要來報導這場高峰會,最後卻被學生占領天安門的事件吸引了過去。
至此,吾爾開希權威的影響力似乎已到了極限。他原本打算釋出一點善意,為戈巴契夫的歡迎儀式清空一半的廣場,藉此展現學生們理性的愛國之心。他才剛說服一群學生撤出一塊空地,空地卻很快地又被另一群人填滿——新來的人是一般支持民眾以及其他更激進的學生。
隨著學生運動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政府內部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出現矛盾衝突,與此同時,學生群眾也因為對運動的發展有不同的想法而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不過,學生們在五月底的一次會議上,罕見地意見一致達成共識,決定退出廣場。但即使如此,在這項共識宣布之時,仍然遭遇一些之前未參與開會的學生反對而開始瓦解。
吾爾開希的逃亡路線
雖然學生們要求民主,但他們卻無法在自己的團體中貫徹民主的原則,完全無視少數服從多數的概念。
吾爾開希還在廣場上的時候,就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告訴一位記者,
「我了解到一件事,民主意識與環境和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我曾說過的,中國改革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它的十億人口及五千年的歷史。」
這個時候,吾爾開希正積極地尋找逃亡路線。
他再次向記者潘文尋求協助。潘文開車將他載到一位北歐外交官家裡,吾爾開希在那兒打聽一些關於政治避難的問題,甚至詢問是否有可能潛入外交使團。「我該去往何處?」據潘文的回憶錄,吾爾開希這麼問外交官。「我坐牢還太年輕了。」鎮壓事件之後,潘文遭指控保護學生組織領導人以及使用非法手段獲取國家機密,被驅逐出中國。
六月三日,吾爾開希在他的學校向一萬多名學生作了最後一次演講。「天安門廣場是我們的,是屬於人民的。我們不允許屠夫踐踏它,」他發下豪語,「我們將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廣場上的學生,保衛中國的未來。」
回到廣場後,他又再次激動地宣誓,他將為保衛天安門奉獻畢生心力,「我可能會被殺頭,也可能流血,但人民的廣場不會消失。我們願意犧牲我們的年輕生命,戰到最後一卒。」
結果,吾爾開希卻在學生最後撤離之前就離開了廣場。
當解放軍部隊開始集結時,他躲藏在一輛載滿傷患的救護車後面,被偷偷帶了出去。救護車開離現場的半路又被攔住,有一群人正抬著一名傷勢非常嚴重的學生。最後這名學生被塞在吾爾開希身旁。這名學生頭部中彈。「我永遠不會忘記,我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抱著一具屍體,」 吾爾開希後來回憶道。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從此展開了漫長的流亡之旅。
頭號通緝犯名單公布了,吾爾開希位居第二,王丹排名第一。王丹決定不逃命,所以他回到北京,當場被捕並被判刑四年;一九九五年他再次被逮捕判刑十一年,後來因保外就醫獲釋,跑到美國去了。
吾爾開希的顯著特徵成了逃亡過程中的阻礙。他和女友劉燕在逃亡香港的途中,一起躲在朋友家、醫院和寺廟裡,和張銘當時採取方法的一樣。他們聯繫了名為「黃雀行動」的地下通道,這條通道不可思議地是由各路人馬組成,例如香港親民主的政客、名人、黑幫,還有西方國家外交官等。「黃雀行動」這個名字取自中國諺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鎮壓行動剛結束不久,二十一名頭號通緝犯中有七名學生成功逃出了中國,其中大部分是受到黃雀行動的幫助。這個行動前後總共將大約四百名異議分子救出中國。幫助吾爾開希逃亡的計畫,大概是黃雀行動最昂貴的一次,約耗資七萬五千美元。香港民運人士透過他們的地下關係(其中包含了惡名昭彰的新義安三合會的五虎成員之一 )利用走私路線將學生帶出中國。
營救吾爾開希時,頭兩次的嘗試都失敗;因為風浪太高,快艇無法靠近岸邊,然後又有軍方巡邏隊破壞了計畫。但是營救行動不管有沒有成功,每一次都要付給把持這條走私路線的黑幫兩萬五千美元。
最後,等了將近一個星期,吾爾開希和劉燕被送到一個偏僻的牡蠣養殖場。他們被告知待在原地,直到水面上出現兩道長長的光照。一旦看到光照打的暗號,就要朝它的方向游去。他們等了又等,等到差點要放棄的時候,終於看到燈打出來了。兩人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涉水出海,奮力游向中國以外的新生活。
一抵達香港,吾爾開希就被一名緊張兮兮的英國官員藏匿起來,並讓他發表一份聲明。聲明影片中顯示,他疲憊得臉色發白,嘴唇顫抖,指責中國政府是「野蠻的法西斯」。
在香港期間,他與華語界的瑪丹娜、流行歌手梅艷芳關係密切,她是協助他逃亡的其中一位資助者。二○○四年,梅艷芳去世的時候,吾爾開希獲准到香港參加喪禮。那時日的香港已回歸中國主權,根據協議,香港自由五十年不變。
當時,吾爾開希的思鄉之情越發濃烈,他跑到邊境處朝聖。在邊界警察的監視下,他將手指伸出了鐵絲網外。「我的手指回到了中國,」他感慨萬分地說。
推薦閱讀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由 八旗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