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是雙重標準?看邱吉爾如何回答「讓中國收回香港」就知道了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邱吉爾從來沒有打算歸還香港,遑論在香港實行自治,更有傳他曾說過:要收回香港,除非在我的屍體上跨過去。
文:邵力競
國際政治一向都是雙重標準;這不是政治的錯,而是人本身的缺陷,好像滿腹經綸的政治哲學家,一旦涉及自己利益,就不見得那麼高尚了。
邱吉爾在書中宣揚的自由、民主,與他的帝國主義是不能調和的,「民主的帝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啊!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是否是西方人說的普世價值,就要看他們對別人有沒有平等對待。
聯合國誕生
1945年初,盟國勝利在望,英、美、蘇三巨頭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高峰會,商討戰後的國際秩序。當時同盟間分歧已現,巨頭們當然明白,人類的紛爭不會隨着一場死掉幾千萬人的戰爭而終結。深謀遠慮的史達林說,在十年內,他們這一批戰時並肩作戰的領袖都會退場,新一代領袖登場,那些人對戰爭的殘酷一無所知。邱吉爾也說,德國早晚會再度崛起,到時候美國大兵都已經回家了,但是法國人卻要繼續做他們的鄰居。這兩個世界級政治家說的話,最後都變成事實。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和平機構,亦是聯合國的前身。由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倡導,原意是希望透過多邊合作,制止侵略,防範再發生大規模衝突。威爾遜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一次大戰是緣於歐洲大國之間的秘密外交、軍事同盟、軍備競賽。雖然凡爾賽和會採納了他的想法,他在美國國內卻無法取得國會通過建議,結果美國沒加入國際聯盟。
沒有了美國的支持,大英帝國成為了國際聯盟主要的領袖。但是英國在一戰後已經無法獨立維持國際秩序,反而奢望國際聯盟的鬆散組織可以替她出頭,制止侵略。結果事與願違,德國與日本因為國際聯盟的制裁而相繼退出,各國如之奈何;二戰的爆發,象徵國際聯盟的徹底失敗。/
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人們需要一個常設機構—新的世界組織。吸收了一次大戰後美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的慘痛經驗,今次美國的參與尤其重要,這個就是現在的聯合國了。

Photo Credit: U.S. Government public domain
當時羅斯福構思的機制是:在這世界組織設一個安全理事會,每個理事國各有一票。任何一項決議須在理事會中取得7個投票贊同(差不多是絕大多數,很民主),方能付諸實行。大事情如制止、解決爭端和提供武裝力量等,則應取得四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當時法國不算在內,所以只有4個)。換句話說,如果美國、蘇聯、英國或中國不同意,那麼安理會是沒有實權的,這就是現在我們熟知的否決權。羅斯福同時建議,如果安理會任何成員國本身涉及爭端,那麼該國只能討論而不能表决,避免利益衝突,理論上合理,但跟後來落實的安排有所不同。
以上做法是吸收了國際聯盟的失敗經驗,因為沒有大國共識的決議,在現實國際舞臺根本是無法執行的一紙空文。
狡猾的史達林
這時候,對人性陰暗面洞悉入微的史達林發言了。他宣稱經過一場災難後,大家都希望至少能保住50年的和平,關鍵在於原來的盟國之間能否繼續維持同一陣線。他始終無法忘記1939年,無法制裁德國侵略的國際聯盟,卻因蘇聯與芬蘭之間的邊境戰爭,把蘇聯趕出了國際聯盟。怎樣才能保障將來的世界組織,不會因戰勝國之間的紛爭而分崩離析呢?
在這段有先見之明的話中,史達林向邱吉爾提了一個狡猾的例子:假定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名義上獨立實際為英國附庸)要求收回蘇伊士運河,那麼英國該怎辦呢?
這時邱吉爾就表露了他的帝國主義觀點:「如果不列顛沒有被說服或者不同意,世界組織的權力是不能用來對付她的。」
史達林問是否真的如此理解世界組織,邱吉爾告訴他確是如此。英國外相艾登接着補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訴,但是沒有英國政府的同意,也不得採取強制執行的決議。美國國務卿也說,除非安理會各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否則不得加以制裁。
邱吉爾認為,世界組織不會取代各國的正常外交關係,會員國仍然可以商討他們之間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組織裡面提出一些可能破壞大國之間團結的問題,將是愚蠢的。
我說史達林的問題狡猾。因為他不過是用了英國自身的難堪處境,問了一道對蘇俄利益攸關的問題。那時候蘇俄早已準備染指東歐,吞併波羅的海諸小國,如果將來英、美在這些事情上跟蘇俄鬧翻,世界組織會否變成制裁蘇俄的工具?現在他從英國人口中得到了保證,可見蘇俄之狡詐。不過,史達林的確眼光銳利,他提出兩個活生生例子,在戰後都發生了:蔣介石要求收回香港不果,埃及獨立後宣佈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觸發1956年的運河危機。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讓英國難堪的是她的帝國包袱。一旦涉及英帝國的殖民問題,邱吉爾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便暴露了明顯的雙重標準。他從來沒有打算歸還香港,遑論在香港實行自治,更有傳他曾說過:要收回香港,除非在我的屍體上跨過去。
那時候他早已經派遣一手籌備諾曼第登陸的蒙巴頓勳爵(Louis Mountbatten)前往印度,準備在德國投降後馬上調兵亞洲,來個亞洲版的諾曼第登陸大反攻,大幹一場,奪回遠東殖民地。只是原子彈提早結束了大戰,英國人才來不及在遠東發動帝國反擊戰,只能派夏慤海軍上將(Admiral Sir C. H. Harcourt)前來香港受降。
不過,令英國最難堪的問題不在香港或埃及,而在印度。
-
本文摘自《亂世領袖學》,天窗出版
作者介紹:
邵力競-生於上海,在香港完成中小學教育,後赴牛津大學攻讀哲學、政治及經濟。畢業後返港,加入港府政務職系,服務十年。離職後,曾在大學兼授公共行政課程,並短暫參加傳媒工作。作者目前正攻讀法律課程。
書籍介紹:
「戰爭中,堅決;失敗時,不屈;勝利時,大度;和平後,善意。」這是英國二戰首相邱吉爾的名言,他自己就是最佳演繹者。
領袖的先見之明,能喚醒一代群眾。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全國厭戰,唯獨邱吉爾看穿納粹野心,力主備戰。其後納粹大軍肆虐歐洲,他以年過六十之齡坐上首相之位,帶領全國軍民,抵抗極權法西斯。
戰後他撰寫了六大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本書作者邵力競將四千頁二百萬字的巨著,抽絲剝繭成七十篇文章,連載於《信報》,備受關注。邵力競在香港官場十年,見盡政經領袖的真實面貌,並以空明洞察力,深入分析邱帥決策背後的重重考慮。
陣前易帥、伸援弱國、犧牲盟友、甚至拉攏蘇俄……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反而是智慧;締結英美同盟,建立戰後世界的秩序,延續英語民族的霸權……又盡顯胸懷大略。作為一代政治家,邱吉爾如何看待殖民統治、自由與民主?在戰爭中怎樣處理種種矛盾的利益與價值衝突?他做出無數兩難決定,判斷力、識見與手腕,缺一不可。閱畢本書,讀者不但會讚嘆其治國方略,更會領略到成為一流領袖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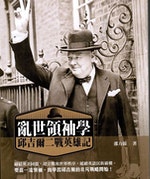
Photo Credit:天窗出版
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楊士範
Tags:
AWSomeDay基礎雲端技術培訓課程,從零開始的企業雲端入門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5月23日下午,AWS即將舉辦的基礎雲端技術培訓課程(AWSomeDay),是為新手量身打造全程免費、半天養成的入門雲端線上課程,歡迎大小企業揪團報名,從企業內部成員開始培養更多具備數位轉型思維與基礎數位能力的核心員工!
在這個「萬物皆能運用AI」的時代,為因應不斷變化的商業市場及客戶需求,全球企業都在不斷加速數位轉型的進程與腳步。據國際調研機構Gartner預測,到2027年時,全球將有超過 70% 的企業使用雲端平台與服務(ICP)來加速其業務,更驚人的是,去年這一比例數字甚至還低於15%。
很顯然的,不只企業遷移至雲端的腳步越來越緊湊、企業內的雲端使用比例與相關支出呈指數增長,企業主對於雲端人才的需求也隨之提升。AWS台灣數位技能研究指出,有70%的受訪雇主表示,他們正在尋求填補數位技能的職位空缺,但其中有過半的受訪雇主表示他們在招聘人才的過程面臨巨大挑戰。
雲端人才不求人:改善企業體質,養成員工雲端素養就是現在!
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嘗試改變思維,從企業內部成員開始「升級」,透過內部訓練培養更多具備數位轉型思維與基礎數位能力的核心員工,以在這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下站穩腳步?
為填補臺灣的數位人才缺口,AWS一年為在職人員提供超過600門的免費培訓課程。其中,專為「初學者」設計,完全免費而且從零開始學習的雲端入門課程「AWSomeDay基礎雲端技術培訓課程」即將於5月23日下午線上舉辦,不論是企業內部的非技術人員、或相關產品服務的技術開發者,都能透過短短3個小時的時間養成最基礎的雲端能力,而完全免費、線上參與的課程形式,也非常適合有數位人才需求的企業、組織揪團報名。

企業數位人才召集令:雲端趨勢、概念、應用完整介紹,打造職場即戰力!
AWS基礎雲端技術培訓課程由AWS資深業務發展經理Annie Lin,以及AWS技術培訓師Joe Huang共同帶領。兩人將深入淺出地介紹雲端基礎概念與技術(如儲存、資料庫管理、運算和網路、資安等), 並結合物聯網、機器學習、人工智能(AI/ML)、生成式 AI 等熱門技術領域。除此之外,這次更特別增設入門證照「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的備考課程,幫助學員取得AWS數位證照,強化企業人才硬實力。
AWSome day線上雲端培訓日 活動資訊
活動時間:2024年5月23日 | 1:30PM - 5:00PM
參與方式:報名完成後,將收到線上觀看連結。報名者只要於課程指定時間上線參與即可。
立即報名:於官網填寫資料即可完成報名。
課前準備:本課程中,專業講師也會分享如何透過AWS帳戶免費使用高達100多種服務,為了讓培訓有更好的效果,請於活動前完成AWS帳號註冊,讓您在課程中可同步操作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