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本文概述與引言
作者余英時在本文即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的政治傳統一向瀰漫著「反智」的氣氛。雖然「表面」上看,中國的傳統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還可以說是比較尊重智性的,但是判斷一個政治傳統和智性間的關係,不能僅從形式去了解,事實上中國的政治傳統也不全然是以反智做為其最主要的特色。
蓋所謂的「反智」,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又稱「反智識主義」,這種現象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可以說是普遍的存在在所有文化之中,雖然不易定義,但基本上則表現在兩個互相關涉的層面: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與懷疑,認為智性即經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於人生皆有害而無益,一般而言,抱持這樣態度的人稱之為「反智性論者」;另一方面則是對於代表「智性」的知識份子們表現出一種餅以致敵視的態度者,這些人則可稱其為「反知識份子」,但他們主要攻擊的對象往往是「知識份子」本身,而非直接針對「智性」而來,但確實或多或少間接對「智性」形成某種程度的否定。
當然,中國政治上的反智傳統不能孤立的去了解,他是由整個文化系統中的各個反智因素凝聚而成。而中國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儒、道、墨、法四家,但墨家又在秦以後幾乎毫無影響,因此,余英時在該文的分析,便僅僅以儒、道、法三家對智性及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為主。
貳、儒家的主智論
從歷史上來看,儒家對中國的政治傳統最為深遠,但是其在政治上不但不反智,反而主張積極運用智性,尊重知識。孔子主張知識份子應該要積極從政,要有用世之志,鼓勵弟子有機會就去改善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出處標準則是要行於「道」。[1]所以他認為不能為當官而當官,更不能為當官而讀書求知。[2]所以孔子事實上是主張知識份子應有原則的積極參政,同時也主張為政者應當隨時注意賢才的選拔,從而挑戰了當時的世襲貴族社會,故其當然較為重視智性。
而到了戰國,孟子曾提出一種分工論,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是一種「天下之通義」,以做為當時提供知識份子參政的理論根據。同時他還主張「專家政治」[3],認為凡欲(能)「治國家」之人必須要是「幼而學,壯而行」的專門人才,蓋因其與冶玉專家一樣,都必須依賴專門的知識。
另一方面,同屬儒家的荀子所關心的卻不再是如何為知識份子爭取正智地位,而是怎樣為知識份子的「政治功能」做出有利的辯護,亦即其在〈儒效〉篇所闡述的中心思想。荀子認為儒者之可貴在其所持之「道」,這個「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嚴守儒家「禮樂教化」的傳統末失。
尤其荀子特別強調知識是政治的基礎,所以其區分儒者的標準,主要在於學問知識的深淺,而將其分成大儒、雅儒與俗儒三類,所以知識必須到了能推類、分類的階段才是系統的知識。舉例言之,他認為大儒就是只能夠「知通統類」,可使其負最高政治責任,而能為「天子三公」者。
荀子主張國家必須尊重知識份子才能興盛和安定,認為須維持一種普遍性的士人政治制度,云:「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蓋儒家的政治思想最主要的智性表現,就在於對於政治批評所持的態度,畢竟儒家論政,往往本於其所尊之「道」,一種從歷史文化觀察所淬煉出來之道,而道高於政,故儒家批評現實政治必然須根據往史的原因即在此。也因此,只要本於此道者,則人人都可以批評時政,庶人當亦可以議政;孟子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者也」的「民本思想」甚至他們對於時政的非議已不限於亂臣賊子,縱使是一國之主或貴為皇帝者,也在其批判的範圍之內。[4]
是以,才有黃宗羲認為知識份子不該是皇帝所馴養的政治工具,應該要負起批評時政的任務,而「鄉學」才是培養知識份子最理想的學校。
參、道家的反智論
一、傳統道家的反智思想
一般多認為道家尚自然而輕文化,對於智性與知識自不看重,[5]不過,即使是同屬道家的老、莊之間的思想彼此也有所差異。
首先,余英時認為莊子對政治不感興趣,主張政府應該越少干涉人民生活越少的「無為(政府)主義」,雖然其基本立場乃是一種「超越的反智論」,但是他從未將其運用到政治思想之中。換言之,莊子對於此後政治上的反智傳統並無直接的影響。
然而,老子就不然了。余英時認為《老子》一書可以說是以政治思想為主體的,故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事實上重點在「無不為」,故道家的反智論影響及於政治應該推老子為始作俑者。蓋他公開主張愚民,認為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沒有辦法有效控制了,不允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以及堅定的意志。所以,他說「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又說:「絕聖棄知(智),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在老子的思想中,所謂的「聖人」不但不需要人民有知識,甚至臣下也不需要有太多知識,所以「不尚賢,使民不爭」畢竟這種競爭反而會讓人民越來越「明」,而非愈「愚」。只有聖人可以無所不知,可窺破政治的最高奧秘,與天合德,此即「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因此,老子的「聖人」能夠自信的隨時集中百姓的意見,並制定永遠正確的政治路線,蓋其無所不知,能掌握一切事物的最高規律──道,也因此他以百姓之心為心,百姓則無從比聖人知道更多,都是不容置疑的。
二、道家與黃老結合的反智思想──黃老道教的反智論
老子的思想在政治上發揮作用,事實上應有賴與黃老思想以及法家的思想和其相互結合起來以後。蓋黃老思想流行於大一統的漢初,絕不是單純因為他提出「清靜無為」的抽象原則,而是黃老與法家匯流之後使得它在「君人南面之術」的方面發展出了一套具體的辦法,蓋統治者對於無法征服的「智性」或「理性」往往最感頭痛,在大一統的君主心中,不同政治觀點的批評具有高度的政治危害性,而得以「亂天下」,故黃老學派對於「智性」與批評政治的知識份子所採取的態度,完全不允許「庶人議政」或「邪說異動」,方才受到帝王的青睞。
黃老的道僅有唯「一」而已,但此一可「長」,而可以引申失之於一切的具體情況,亦即「放之則彌六合,卷(捲)之則藏於密」、「一之理,施於四海」的普遍真理。唯有了解這個真理的人,才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換句話說,他不但永遠正確,而且懂得一切事物的規律。
另外,《漢書》〈刑法志〉云:「聖王置諫諍之臣。」儒家的道是超越性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絕非帝王所得私者。然而黃老的帝王在理論上則是「道」的壟斷者,因道即唯「一」[6],故「聖王是法,法則明分」,也因此他永遠正確,是一切言行的最高標準,何需他人之諫諍或批評呢?
是以,從理論上來說,黃老道教的反智根源即是建立在其「一道論」之上,道統和正統實際上乃是「合而為一」的。也因此,在黃老一道觀的社會裡,只有帝王可以「持一以正臣民」,臣民無從立足。畢竟,黃老和法家的觀點基本上是相同的──君臣關係是絕對而永遠不能改變的。故黃老真正思想關鍵,一言以蔽之就是「得君行道」而已。
肆、法家的反智論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就摧殘智性或壓制知識份子的部分言之,法家的主張都是最徹底的,也因而使得反智論得到高度的發展。
法家關於一般性的愚民政策主張,是排斥智性最清楚的指標,基本上其策畫出一套具體的實施辦法,首先即表現在《韓非子》〈五蠹〉之中: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
韓非子這一見解,成為後來秦始皇焚書的理論根據,蓋其意思是說除了法以外就不許有任何書籍之存在,而歷史記載與先王之語,亦不能獨外其中。所以國內僅能允許留下兩種人,一種就是廣大的勞動人民(主要是農人與工人),一種就是軍隊,以為「富國強兵」之用。至於人們想要學習與了解文化者,就必須以國家官員為師,並以法家的政治路線為唯一學習之對象。而這樣的主張也在秦始皇與李斯的政策下在當時被徹底的執行。
而韓非主張愚民就是因為他從根本上就認定了人民是愚昧無知,無法了解國家最高政策的涵義。如果再讓他們擁有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就只有更增加政府執行政策時的困難,尤其他在〈顯學〉一篇的思想主張就連孔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都相形遜色不少。[7]
至於,戰國晚期商鞅的《商君書》在愚民政策中也有不同的發想,其重點主要放在防止知識份子和國外發生聯繫,而影響到國內的政治路線。也因此法家的政治路線必須以禁止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與國外互通有無為其先決條件。畢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政教合一」的,也因此,在國內只能有一種思想的標準,方才能收「萬眾一心」之效果。
而《商君書》〈算地〉篇與《韓非子》〈五蠹〉篇都曾特別針對戰國時代的五種人來加以批評與攻擊,而知識份子顯然是首要的攻擊目標,此乃因「夫治國捨勢而任說(談)說,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一如韓非所言的:「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之意。原因無他,僅因知識份子喜批評時政,對於法家政權的危害性最大,會導致人民「輕視國君」(輕其君)和「誹謗朝廷」(非其上)之故也。換言之,這五蠹(民)對於政治的危害性,恰好就是來自於他們的專業知識或技能。甚至如果,國內這五蠹(民)大量充斥時,法家也不在乎,畢竟國家擁有軍隊,必要時當然可以動用武力鎮壓之。
不過,嚴刑峻罰也僅是法家鞏固其統治基礎的消極辦法而已,在積極面上,《商君書》〈賞刑〉還主張:「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白話言之,所謂「壹賞」係指高官厚祿之賞專保留於有軍功(斬首)之人,;「壹刑」則指除了君主以外,凡有作亂犯上者一律處死;至於「壹教」便是統一教育、統一思想以及統一價值標準,故壹賞和壹刑在此便成了壹教的雙重保證,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相當於黃老「一而二,二而一」的一道觀,而統一的教育當然是由身為「聖人」的君主來制定了。
也因此,在法家思想的統治下,凡是一切有德行、有學問以及有技能的人,基本上都不能透過其來取得政權,通往政權的門只對善於斬首之有軍功者敞開。畢竟,法家對於人性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是好權勢與財富的(適合因循利誘),而且是貪生怕死的(嚴刑峻法阻嚇),也因此人的思想永遠是趨利避害的。
法家的反智論基本上和其「尊君」的主張是密不可分的。而知識份子對於國家的政策或者君主的想法往往不肯死心他的的接受,甚至有時還會提出質疑或批評,難免會使統治者聞而生畏。然而,法家的尊君論在積極方面表現在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萬不可大權旁落,造成君弱臣強的情形發生;而消極方面則是必須超乎一切批評,君主縱有過失,也是臣下擔責,故「尊君」必定「臣卑」,並因此而成為法家思想的最高指導原則,終而使得這樣的指導原則,成為秦朝日後以「焚書」作為其基本國策的依據所在。
伍、儒學的法家化─從主智到反智
學者一般多認為,從漢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思想的百家爭鳴時代似乎就已經正式成為儒家獨霸的局面,尤其近代學者在攻擊儒家思想在歷史上往往與君主專制互為表裡時,確實也常常以漢武帝的「復古更化」為其始點。
然而,在秦始皇時不容存身的儒學,又面臨漢高祖劉邦最鄙視儒生的窘境,但是儒學在漢武帝時竟能夠「定於一尊」,此時其在政治性格上,事實上已經發生一種根本性的質變,余英時認為這是一種漢初儒學發展的特殊情景,此即「儒學的法家化」。
漢代儒學法家化現象始於叔孫通,雖然劉邦鄙視儒生,但是叔孫通所制定的「朝儀制度」卻深受劉邦的賞識。蓋叔孫通曾任秦廷博士,其所定朝儀乃「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施行「尊君卑臣」的禮節,並主張「人臣無過舉」,從此使得尊君卑臣成為儒家政治的一部份,故其朝儀施行以後引劉邦嘆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8]是以,余氏認為叔孫通時為漢代第一個將儒學法家化的「儒宗」。
接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公孫弘,則是「兩面派」的開山祖師。[9]他極力維護君主的尊嚴,不願傷其半毫。《儒林傳》中評:「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識靡然鄉風矣。」故自公孫弘以後,大批的法家開始改頭換面變成了儒生,從而更加速了儒家法家化的腳步,此與其以「儒術緣飾吏事」之舉絕對脫不了干係,[10]所以帝王要殺人,除了引據法律條文之外,甚至還必須回到儒家之經典中找尋依據,亦即「經義斷獄」。[11]也因此,犯人不但死於法,甚至還死於理,也因此更無可救。董仲舒為此甚至還出了一部《春秋決獄》[12],將《春秋》化為法典,而成為儒家法家化的最重要例證。
馬端臨在其《文獻通考》卷182中評論《春秋決事比》時,可謂直搗核心,沉痛地揭露了漢代春秋斷獄的真相:
《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靈異對之類耳。(武)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因緣假飾。往往見兩傳[13]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
換言之,追源溯始到最後,「以理殺人」的傳統絕對是和「春秋斷獄」分不開的,也就是說,這是「儒學法家化」的一種必然結果。且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只限於漢代,實則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的政治史,及至明清亦同。畢竟皇帝們所關心的「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就算是晉室「君弱臣強」的局面,也仍然會嚮往著法家的路線。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長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熄,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
也因此,董仲舒要用儒家來代替法家的正統,以《春秋》的大一統來取代黃老的一道觀與法家的壹教論。並且透過利誘的手段,明白表示只有獨儒家之經典才有官做,因而開設五經博士。
另外,他將法家的「三綱五常」以及「尊君臣卑」的觀點「偷渡」引入《春秋》的教義之中,同時也把這樣的原則推廣到其他各種的社會關係方面,而這也導致後世批評儒家尤其集中於「三綱」之上,但是這完全是對儒家與法家思想不了解或有所誤解之人才會有的批評。
不過,余英時認為董仲舒並未完全脫離儒家的立場,也因此他才會想透過「天人感應」等陰陽五行的學說來限制君權,所以他才不甘心把「道統」整個託付給「帝王」,才能對湯武革命加以肯定,甚至還能透過春秋之義來「貶天子」,由此可知董仲舒多少還是有受到「庶人議政」的傳統的影響。
最後,余英時用朱熹的話做結,認為事實上儒家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在這2300年之間,實未嘗一日得行天地之間也。
陸、結論
道家思想體現在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上,配合著「絕聖棄智」的「政策目標」,就容易在有效控制人數增長的情況下,達到「愚民」的目的。畢竟,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之重點在於「無不為」,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沒有辦法有效控制了,不允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以及堅定的意志。
然道家思想與黃老治術做結合以後,以「清靜無為」作為人民生活的最高指導方針,並以黃老思想「得君行道」作為其核心價值,使得人民僅需奉行君上之意志為意志即可,與君上合而為一,蓋黃老的帝王在理論上則是「道」的壟斷者,因道即唯「一」之,而道統與正統本是一體兩面之故也。
至於,中國政治思想中最反智的法家,主張「尊君卑臣」,並且從「深層假定」認為「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所以人民根本上就是愚昧無知的,無法了解國家最高政策的涵義。此時若再使其求知,擁有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就只有更增加政府執行政策時的困難,加上,人民竟然蒙昧無知,則難保其曲解智識,誤判情勢,反而容易危害蒼生社稷。畢竟,人民之心智永遠不如君上來的成熟,最好的辦法就是服從於君主的領導之下。加以,法家對於人性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是好權勢與財富的(適合因循利誘),而且是貪生怕死的(嚴刑峻法阻嚇),故人的思想永遠是「趨利避害」的。也因此,法家認為最好的統治方法就是使賞罰分明(壹賞壹刑),並且要重賞嚴刑才是。
最後,談回儒家。
長久以來,大家對儒家的思想似乎一直都有很深的誤解,基本上,儒家的思想中心是「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要盡份內事等等。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強調「民本思想,主張「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故會有「聞諸一夫紂也,未聞弒君者矣」之言論產生,其實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
有人主張「儒家其實是一種宗教,而且是政教合一的」,因而認為最高層的統治者便是儒教所謂的「聖王」,身體力行著儒教的教條,人民必須服從他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的領導,造成有儒教思想滲透的土壤,非常容易培養出獨裁者,這完完全全是一種對儒家的誤解。
事實上,儒家最原始的思想是「主智」的,既「非愚民的治術」亦非「反智的存在」。然而,為什麼許多後人在後來理解儒家思想時常常會造成誤解呢?其實,從漢武帝採董仲舒之議,而奉行「陽儒陰法」之政策指導方針,而將儒家與法家的思想內涵混為一談時,就已經造成儒家思想傳至後世,某種程度上已經逐漸變成君主用來駕馭人民的治術,形成「儒家的法家化」。其特色就是將法家的「尊君卑臣」與「三綱五常」觀融入在儒家的思想之中,蓋儒家思想本是普遍適用於一般大眾之上,在此時已初步被導入了「階級」的觀念,並因此造成兩者之間的調和鼎鼐,史的儒家的「主智」從此變成了「反智」的愚民治術。
甚至,一直到了宋代朱熹以後,開創宋明理學,主張「大義名分」論,強調君臣父子之間等應守的節義和本分,「尊王勤王」反而使得儒家的思想更加的被扭曲,到後來更發展到了極端,與釋家佛學思想的「宿命論」、「唯心觀」相互結合的情況下,反而使得儒家反智到一種幾乎無以復加的境界,讓人民「愚的愈愚,奴的愈奴」,而且在宋明理學(朱子學)被引進到日本以後,融合了日本特有的神道教思想以及武士道精神後,就又更進一步地被發展成具有極大侵略性的「軍國主義」思潮,[15]高唱大東亞共榮圈的「毀滅性基調」,反而,造成整個東亞在近代時局所發生的一連串的慘不忍睹的悲劇。**********************
※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 一文出自: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1976)。
[3] 《孟子》〈梁惠王下〉:「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4] 例如董仲舒即有「貶天子」之說。而東漢以後所出現的種種政治活動與社會抗爭,往往也無法跳脫「庶人議政」觀的影響。另外,東漢的太學與明朝的東林運動亦可見之,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學校篇〉就曾提及之: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
[6] 儒家則為二道論者,將其分為「道統」與「政統」,肯定道統高於政統,如依據道統之標準,則臣下亦可批評代表政統的君上,是與黃老道教之一道論不同之處,蓋黃老道教的道和政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此明顯表現在其之〈九主〉篇中。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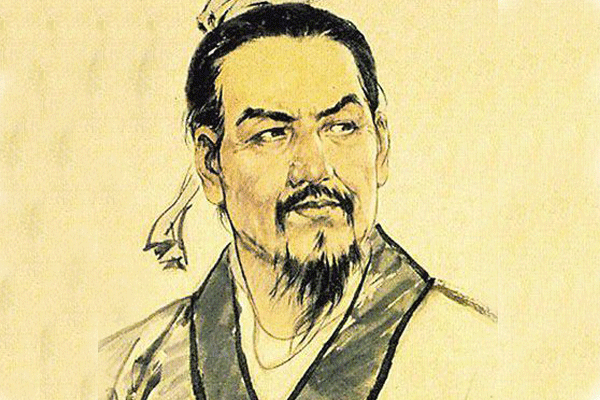
﹝韓非子畫像﹞
﹝左:孔子畫像;右:老子畫像。﹞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