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他們是人,不是道具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大體老師經血管注射福馬林以後,要放置在遺體儲存室長達三至四年才會啟用,也就是說,他們早在這些醫學生入學以前,就已經靜靜在學校裡等候了。這群老師們在他們生命終了之後,遺愛人間,提供他們的軀體,讓醫學生解剖下刀,以做好將來行醫的準備。
在醫學院,有一群很特別的「師資」,用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來傳道、授業、解惑,他們給學生的,是貨真價實的「身教」。我們稱他們為「大體老師」。
這群老師們在他們生命終了之後,遺愛人間,提供他們的軀體,讓醫學生解剖下刀,以做好將來行醫的準備。
第一課:特別的老師
因為華人普遍期待「保留全屍」的文化忌諱,早年供做解剖用的遺體來源極少來自自願捐贈者,多半都是路倒的無名屍,或是沒有親人的榮民遺體,這些遺體經過公告三天之後,若無人領回,才會分發到各醫學院做防腐處理。
所謂的遺體防腐處理,通常是以福馬林(即37%甲醛溶液)、石碳酸、酒精、甘油和水調配為防腐劑,以浸泡或注射進血管的方式,讓遺體經久不腐。傳統處理方式為經血管灌注防腐劑後,再將遺體浸泡於10%的福馬林溶液。
用浸泡方式處理的遺體味道極為刺鼻,學生上課經常被刺激得眼淚鼻涕直流,但對於狀況較差的遺體有較好的防腐效果。早期各醫學院校多半都是採用浸泡方式防腐,作法是在實驗室裡設置像小型游泳池般的大型水泥槽池,注滿福馬林,再將別好吊牌的遺體一具具浸泡在其中,用木板壓在上面,使遺體長時間浸泡在福馬林中達到防腐效果。
因為體表及腸道內細菌的作用,一般來說,在溫度攝氏二十度左右,屍體的組織只要經過四十八小時,即會出現明顯的屍斑與氣味,當年大體老師的來源多半是無名屍,且絕大多數都是男性。他們被發現時,遺體的狀態可能就已經開始產生變化了,但在被發現以後,還要經過三天公告無人領回,才能分發到各大醫學院用作解剖教學,因此早期解剖教學防腐處理的遺體,很多時候情況都是不太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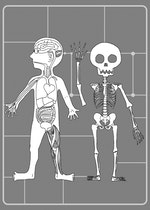
記得以前在其他學校擔任助教時,曾處理過一具遺體,已經散發出濃烈的腐臭味了才被送來,即使我們都已經對遺體氣味習以為常,但那一具遺體的情況實在太糟,組織開始分解,屍胺氣味濃到口罩也擋不住,我們在進行防腐處理時,三個人必須輪流出去嘔吐,才能把工作完成。
因為早期大體老師的來源實在太少,數十位醫學生才能分配到一具遺體,即便是現在,許多醫學院還是得十幾個學生使用一具遺體,這麼多人擠在一個解剖檯旁,不是每個人都能親手解剖各個部位,學習效果多少會打折。
他們是「人」,不是「道具」
用做大體解剖教學的大體老師,必須在去世後二十四小時內送來;用做模擬手術的大體老師,更須在八小時內就送來,就專業上,我瞭解這要求的必要性;但在情感上,卻覺得非常不忍。
想像自己至親若是過世,連一個簡單的告別式都來不及辦理,就得強抑痛失親人的哀傷,要冷靜下來處理捐贈事宜,聯繫、安排救護車,儘速把摯愛的家人身軀,一路顛簸送到花蓮,進行防腐處理或急速冷凍,然後,是長達一至四年的等待。這教人情何以堪?
無論是大體老師或他們的家屬,若不是心中懷有寬厚慈悲的大愛,如何能做到這一點?
面對如此深情又沉重的一份託付,我們誠惶誠恐、不敢辜負。
我們希望學生們在大體解剖學這門課中,不只學到了解剖知識,更能學到怎麼待人處世;希望學生在解剖時,不只是把解剖檯上的身軀當做學習的「道具」而已,而是一個「人」,跟你我一樣,是個有喜怒哀樂、有故事的人。
因此,我們學校要求學生在大體解剖課程開始前的暑假進行家訪,拜訪大體老師的家屬,從家屬的口中認識未來將以身示教的這位老師。
早期我在其他醫學院擔任助教時,有時候不禁會有些憤慨,因為學生們只是把解剖檯上的大體老師當作學習工具而已,也許是為了掩飾緊張的情緒,也許是無心,學生偶爾帶著輕率的態度開起遺體的玩笑,毫無尊敬或感恩之心。
學期末考完試以後,這些供學生學習的遺體經過一學期解剖,運氣好的,被支解的手腳軀幹等被完整的收納在同一個屍袋裡,但很少有學生問及「接下來呢?遺體會如何處理?」。在那個年代,剩餘的善後工作通常是由技術人員負責,將收拾在屍袋中的遺體送去火化,遺體的角色對學生而言只是學習的工具。
我受嚴謹的科學訓練,又從事解剖教學,按理說應該會很鼓勵親人捐出遺體,但因為擔任助教時在課堂上看過許多學生冷漠的態度,以及他們處理遺體的方式,當年我的母親想要簽署捐贈大體同意書時,希望我在家屬同意欄簽名,卻遭到我強烈反對。一想到我深愛的母親可能會這麼慘不忍睹地被「使用」,最後還像廢棄物一樣被隨便打包處理,我就心如刀割,這份同意書怎麼簽得下去?
這種態度,一直到我到慈濟大學任教才改觀。學校對於大體老師的態度十分慎重,也要求學生們必須以同樣的慎重對待。
我們希望學生們能把大體老師當作「人」,而非「物品」看待,畢竟醫生是一個救人的行業,我們期盼這些孩子們將來行醫時,能有更多的體恤與仁心,瞭解他們所面對的,是「人」,而非一具還活著的器官組合。
早早等候著的老師們
也因為如此,學校才會要求學生必須進行家訪。雖然台下的孩子們都已經是大學生了,但出訪前,講台上的老師總是叨叨絮絮提醒學生,不厭其煩叮嚀著拜訪大體老師家屬時要留意的細節,包括約訪的電話禮儀、拜訪當日的服儀……等等,偶爾也會擔心學生們會不會覺得老師們太囉唆,小看他們了。
但,我們有慎重的理由。
大體老師經血管注射福馬林以後,要放置在遺體儲存室長達三至四年才會啟用,也就是說,他們早在這些醫學生入學以前,就已經靜靜在學校裡等候了。
我們學校的遺體儲存室位於解剖講堂旁,中間隔著一條走廊,沿著走廊有大扇玻璃窗,平常會用木製拉門遮住。遺體儲存室的陳設有一點像學校宿舍的上下舖,大體老師整齊躺在那裡,拉開玻璃窗上的拉門,隱約可以看到大體老師的輪廓。
在等待的漫長三、四年中,每逢清明、年節或是大體老師的生辰、忌日,許多家屬都會特地來這裡遙望致意,有些家屬還會在遺體儲存室外牆的大體老師姓名牌旁邊,留下寫滿思念的便利貼或小卡片,我偶爾會到這條走廊上看家屬給大體老師的留言,這些留言真的非常催淚。
「我們會非常慎重對待您的家人,請您安心」
這幾年,我更常走到遺體儲存室外,因為裡面有我認識的人。蔡宗賢醫師,我們都稱他宗賢爸爸,我們帶過同一班學生,曾經與他聊天,看著他具感染力的笑容、聽著他熱情的述說他的人生經驗。他生前是一位牙醫,雖然因為小兒麻痺身有殘疾,但他心地無比美麗,儘管行動不便,但仍每週不辭辛勞到偏鄉義診,八年從不間斷,足跡累計超過三十二萬公里,可惜天不假年,正值壯年就病逝,死後捐贈大體遺愛人間。
在他名牌旁邊,貼著好幾張寫著摻雜注音、筆跡稚拙的便利貼,上面寫著:「爸爸,ㄓˋㄨ 您父 ㄑㄧㄣ 節快樂,您好好.ㄛ,因ㄨˋㄟ我 ㄓ 道您ㄉㄡ ㄉˋㄨㄟ我ㄏ✓ㄣ好,ㄙㄨ✓ㄛ ✓ㄧ我會好好ㄉˊㄨ書,ㄖˋㄤ您放心的」、「爸爸,我想您在ㄌˋㄧㄥ ㄨˋㄞ一個ˋㄕ ㄐˋㄧㄝ 了吧,我好愛您.ㄛ,我想您還會做我爸爸的」……
刻骨的思念,溢於字裡行間,像這樣深情的留言,還有好多好多,雖然已經看過許多次,但每一次看,仍覺得眼眶發熱,也愈發覺得自己責任重大。
對家屬來說,他們親愛的家人彷彿還活著,在正式啟用前,他們都是懸著心在等待的。經過了三、四年,當「那一刻」真正來臨,對家屬而言,肯定是百感交集,我們希望清楚讓他們知道:我們會非常慎重對待您的家人,請您安心。
大體老師啟用典禮
在大體解剖學課程開始之前,學校會舉辦一個正式的啟用典禮,邀請大體老師的家屬也一起來參加,提醒學生也承諾家屬:課程即將開始,我們將用心學習。
暑假家訪之後,各組學生都要整理大體老師的生平,在啟用典禮之前做行誼簡介,跟大家介紹這位特別的老師,每一位大體老師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他們的大愛與胸襟,著實讓人動容。
有位大體老師生前告訴家屬:「雖然我書念得不多,但是想到能當醫學生的無語良師,我就很高興,非常高興。」
而另一位大體老師彌留之際,喃喃囈語著:「我要去上課了……」、「三天……」這些聽起來似是臨終前無意義的言語,在三年後,因為學生的到訪,家屬有了新的解讀:「因為天上一天,人間是一年。」
行誼簡介完,接下來就是啟用典禮。會有一個簡單隆重的宗教儀式,然後由醫學生揭開覆蓋在老師身上的往生被,供家屬瞻仰遺容,這是這三、四年來,家屬第一次這麼靠近他們的親人。
啟用典禮之後,還有一個簡單的茶敘,讓學生與家屬交流。有些家屬會殷殷叮嚀說:「我媽媽很怕痛,你下刀要輕一點喔。」也有家屬很豪邁的告訴學生:「你放心,盡量割,重要的是好好學 !」無論是要學生審慎一點,或是大膽一點,我都覺得是非常好的提醒。
不過醫學系的功課實在太重了,解剖學又是要求極為嚴格的一門課,啟用典禮後那種澎湃高昂的「熱血感」,在學期開始之後,就會被壓力慢慢磨損,取而代之的則是疲勞與挫折感。不過,我相信大體老師的託付,在孩子們心中已經埋下了使命感的種子,提醒他們莫忘初衷。
書籍介紹
《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那些與大體老師在一起的時光》,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何翰蓁、李翠卿
從第一堂課手的解剖開始,到學期末和大體老師面對面,十堂嚴格又緊繃的解剖課,道盡對生命和身體知識的熱愛。
身為大體解剖老師,在母親想簽署捐贈大體同意書時,為什麼強烈反對且痛徹心肺?解剖檯上的大體老師,難道只是學習工具和器官組合嗎?他們也是有故事、有溫度的人!
大體老師生前最後的願望是什麼呢?若有機會跟學生面對面對話,他們會想說些什麼呢?大體解剖課在醫學系可說是一門最令人聞風喪膽的課,負責的老師一個比一個凶悍。為什麼這群「活」老師對這群聰明的學生如此嚴格?他們居心何在?
對醫學以外的人來說,解剖學深奧複雜,對大體是既好奇又害怕。解剖室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醫學生如何忐忑切下第一刀?一學期相處下來,大體老師和學生之間產生什麼樣的特殊情感?
身為解剖課的「活」教師,本書作者串連成長點滴,寫出內心世界,既述說自己在解剖現場的經歷,也描繪了學習過程中醫學生內心的觸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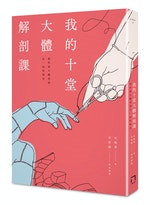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楊之瑜
Tags:
芥菜種會「三福助人網」串聯全台社區網絡,助力社會安全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期保母虐童的事件延燒,使社會再度檢視由社政衛政支撐運作的社會安全網,若能在政府或社福機構資源無法觸及的角落,建立相對健全、互助的社區網絡,相信這樣的助人網將會成為社安網的助力,並帶給台灣社會共生共好的永續價值。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那個需要受助的人,而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在地社區助人網的一份子!
近期保母虐童的事件延燒,使社會再度檢視由社政衛政支撐運作的社會安全網,因在不同環節出現的聯繫斷裂,導致憾事發生。在「剴剴案」發生之後,4月中台北市家暴防治中心亦接獲一名全日托兒童疑似受虐的通報,然而受到媒體關注的只是少數極個案,但我們都知道還有隱藏在檯面的聲音需要被聽見,更多需要協助的弱勢。
政府推動的社安網量能有限,近年社福及保護案件數量上升但社工人力卻持續短缺。根據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於2020年所作之社會工作系所就業調查,全台社工系所畢業生僅有25%投入社會工作。此外,社工工作的高壓也造成徵才困難,以新北市為例,2022年社工師離職率達7.49%,有141個缺額難補;台中市近五年來受虐兒童人數增加1倍,但社工人數自2019年至2022年僅增加約4成,而2024年台中市社工師仍有7.8%之人力缺口。
今年3月衛福部曾一度提出提高社工訪視頻率的主張,引起社工團體強烈反彈,在目前已經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貿然增加訪視頻率並非改善社安網的解決之道。此外,中華民國兒童權益促進協會(兒權會)4月27日也在凱道舉行集會,呼籲行政院應成立兒少權益辦公室,整合原本四散在中央與地方各機關的兒少保護業務,並通盤檢視現有的出養安置制度等訴求。
政府社安網不是萬靈丹,透過民間、社區的互助資源,有時更能提供不同面向的實際支持:以日本高齡化社會為例,他們打造失智症友善社區,將相關知識帶入地方,讓社區民眾與店家能及時協助走失的失智長者;在英國則有以社區為核心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結合地方政府、家庭與臨床醫學部門等單位,試圖讓個案接受不同社會資源的幫助,同時也使其順利重新回歸社區。或許在兒少保護與協助家庭功能恢復方面,也能透過社區網絡助力社會安全網。
讓社區力量成為社會安全網的助力
相比於社福機構的定期預約訪視,與孩童或脆弱家庭更密切接觸,且更能即時發現問題的其實是學校、里長、教會、愛心店家等社區網絡。以芥菜種會為例,他們積極連結社區合作夥伴建立支持網絡,透過關懷訪視扶助中的家庭,以及以及社工督導帶領關懷志工團隊進入社區陪伴等方式,讓社區多一雙眼睛、多一對耳朵,提供「看得見,聽得到,走得到,接得到」的服務,協助因貧窮、風險與多重問題需要支持與介入的脆弱家庭,從「家的照顧」逐步落實「家的恢復」。
此外,芥菜種會也設立通報機制,提供民眾透過「找幫助」QR Code 及援助專線等管道主動求助,相關資訊都印在廣發的文宣品上,關懷志工團的「安安」過去就曾是藉由這個管道尋求協助的社區需要者。當芥菜種會接收到求助訊息後,會迅速評估狀況並提供有效支援,幫助家庭渡過當下難關,後續的地區助人網則以生活關懷等方式協助家庭恢復。
「基萬金」三福助人網提供工作機會,陪伴單親媽媽重新出發
除了提供急難補助與物資,芥菜種會更致力於建立系統化的培力模式,提供受助者工作機會,獲得一技之長並賺取薪資得以自立,讓受助者得以成為助人者,進而再投入到社區中。芥菜種會執行長李肇家表示,社會的穩定源於家庭的穩固,家庭穩固的根本,不在兒少與青年,而是在照顧者(包含原生父母、類父母)的健全。芥菜種會透過一對一陪讀、親職課程、職業培力等方式,致力促進家的恢復,陪伴家庭照顧者克服階段性困難並提升親職能力。

2023年芥菜種會在基隆、萬里、金山等一帶,建立首個助人網絡「基萬金」三福助人網,以孫理蓮紀念營地為主要據點,連結周邊學校與社區等單位共同協助弱勢學童。此外,也提供營地相關的房務、廚務、販售等工作機會給需要者。單親媽媽安安就是透過三福助人網,在營地擔任房務人員,在自力更生的同時也能將年幼孩子帶在身邊就近照顧。
建立100個共生共好的助人網
在面臨急難變故時,即時物資救助與安置能夠解決人們的立即性需求,而政策性的津貼也許能夠給予脆弱家庭經濟上的支援,然而家庭功能的恢復則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不論是在心靈層面上從創傷中走出來,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重拾能力,需要者周邊的資源都扮演重要角色。若能在政府或社福機構資源無法觸及的角落,建立相對健全、互助的社區網絡,相信這樣的助人網將會成為社安網的助力,並帶給台灣社會共生共好的永續價值。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那個需要受助的人,而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在地社區助人網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