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原住民日!荷蘭人對臺原住民的「文明性」是如何形成?

第一章 「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
一、前言
自哥倫布開啟歐美新航路以來,歐洲世界對異族的想像逐漸納入領土占領、宗教改宗、經濟利益等思維。其中,對土著民族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描述,一般多為實施領土占領、建立殖民社會的前奏。此係藉由自許為導入文明至「蠻荒(wilderness)」領地,並將土著視為非「蠻」(barbarians)即「番」(savages)來合理化其作為。雖然日後孟德斯鳩(Montesquieu)透過階序化的差別分類與社會演化意涵角度,發展出分辨「蠻」與「番」的概念;前者為略具政治組織的草原游牧民族,後者為生活於林野中的採集或狩獵群居團體,以此來分辨文明化程度的差異;並以財產的私有化做為判定兩者差別的準則之一。不過,一般來說,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人,縱使在理性層次上傾向於以其對羅馬法的詮釋──即以私有財產概念的有無來判定對方是否為「文明人」,基本上仍存在著藉由諸如食人(cannibalism)、人祭(human sacrifice)、裸身等社會文化行為來辨別他者的「文明」與否。
十七世紀東渡來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即處於此異族印象論述形成的過程,作為其日後治理當地屬民的律法基石。當時,東印度公司面對臺灣島上的南島語族,係透過地方會議、村社首長、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及贌社等制度,達成所謂「荷蘭和平」(Pax Hollandica),逐步將南島語族置於其轄下,將臺灣拓展成其轄下第一個領地型殖民地,企圖在島上建立起如後世史家所說的地域型國家(territorial republic)。東印度公司在臺的政令依據,即涵括荷蘭人對當地風俗的掌握與理解。作為行政中心熱蘭遮城腹地的大員灣一帶,為臺灣長官與議會接觸較密集之處,針對當地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等社的討論,自公司領臺起即成為荷蘭人筆下的福爾摩沙人(Formosans)代表,其風俗習慣,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首要參照;不過,荷蘭人在臺灣不同地區的「南島語族經驗」,不盡然與行政中心大員灣一帶的經驗一樣。東印度公司在臺30餘年期間,隨著領地範圍的擴大,接觸的島上人群也愈來愈多,其官員對不同人群的「文明化」程度也有著不同的評價。
本章即討論東印度公司官員對臺灣不同地區住民的「文明性」論述,以及其形成背景。並討論公司30餘年的統治與住民教化工作,如何與時俱進形成其整體的臺灣住民「文明性」論述。文章先描述甫抵臺灣的東印度公司官員如何看待大員灣一帶的住民,並由公司在領地擴張過程中,官員筆下三群「文明人」的特質,探討形成其個別「文明性」論述的原因;並以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為例,討論公司官員在中介影響下的負面認知,以及對臺灣原住民施政的影響。接著討論東印度公司在臺初期的「文明化」作為,並舉一較極端的小琉球人案例,討論荷蘭人如何實踐其殖民地的文明化理念。最後析論隨著統治與住民教化工作的進行,公司官員如何將全島住民區劃成不同的「文明化」評價,以及其內容為何。
二、驚鴻一瞥
初抵臺灣的荷蘭人,對原住民的認知與理解,往往來自道聽塗說、短暫接觸所留下的表面印象。早在1622年,爪哇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派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率艦隊前往澳門、澎湖一帶,替東印度公司尋求適合的貿易據點時,提及依據所探得的唐人說法,與澎湖一水之隔的臺灣為富饒之地,但當地住民為群「易怒且全然不可靠的人民(een boos ende gans trouweloos volck)」。
1623年,雷爾生為了決定在北臺灣的淡水、雞籠,還是南臺灣的大員設立商館,派員前往調查;訪查重點含港灣、土地,以及四周的住民。4月,從別稱唐山甲必丹(Capitain China)的李旦與負責探查的上席商務員Adam Verhult那所獲得的消息是:淡水、雞籠住民是「非常凶殘的人民(seer moordadig volck)」,無法與他們溝通。之後,加上別稱漳州長鬚(Langenbaert wt Chincheo)的Houtamsong提供的資訊,雷爾生所留下的紀錄則將雞籠灣說成是無法避東北季風之處,因此不適合船隻停泊;附近海灣高處的住民是「野人(wilt volck)」。至於雀屏中選的大員灣,訪查的對象是蕭壠社人,負責造訪的是商務員Jacob Constant與Barend Pessaert,留下了較豐富的民族誌描述與評論。
Constant與Pessaert筆下的蕭壠社人,是群高大、魁梧、奔跑神速、體型優美、身軀結實,深得自然宏恩的民族;成人膚色如摩鹿加群島的Ternate土著。蕭壠社人雖裸體走動,但相對無愧,因而成為Constant與Pessaert看過的所有民族當中,「較貞潔或不具淫蕩想法的(in luxurie ofte oncuysche begeerte minder sijn brande[nde])」。不過,當地人因不對夫婦、父子、長幼、官民之別表現謙卑、尊敬或敬畏,來去自如,為所欲為,也不受Constant與Pessaert所認知的法律所束縛,或表現出驚懼或尊重,因而養成其「野性、番性(als die wilt ende woest opgevoet sijn)」的一面;不過,其人民因「談吐幽雅,謙遜緩慢,讓人感到悅耳。若從其談吐來認定,則絕非野人(geen wilde),而是秉性善良,一身謙遜,具智慧的人。」

雖然Constant與Pessaert對蕭壠社人的言談舉止方式有正面的評價;不過,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依然成了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此一標準,亦反映在當時東印度公司其他官員認知上,爪哇總督與議會紀錄的《巴達維亞城日誌》,強調蕭壠社人「裸體走動而不覺羞恥」,屬於相當「狂野、野蠻的人群(wilde ende barbarische menschen)」。出巡馬尼拉的艦隊司令Pieter Jansz. Muyser給總督Pieter de Carpentier,以及給阿姆斯特丹十七董事(Heren XVII)的信件,提及大員灣一帶的目加溜灣、蕭壠和新港社人,是群外出完全赤裸、不斷從事殺戮、沒有臣服於任何法律或社會秩序的「粗俗野蠻人(rouwe barbarse menschen)」。
如果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是當時荷蘭人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那麼,臺灣島上的確有住民可博得東印度公司官員的「文明人」封號。1636年,東印度公司藉由與「野人」盟社的聯合武力征伐,讓臺灣南部平原大部分的原住民村社,以與荷蘭人結盟為名歸順於公司的名義統治。之後,順勢南下企圖繞往東部的荷蘭人,探得了一群「文明人」──屬排灣族的瑯嶠(Lonckjauw)人。
●本文摘選自聯經出版之《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
逛書店
延伸閱讀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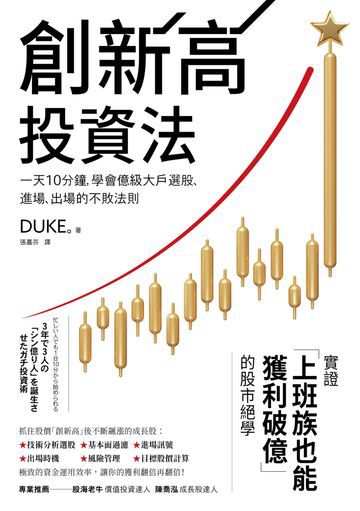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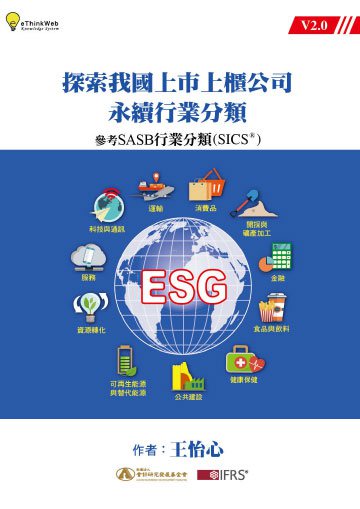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