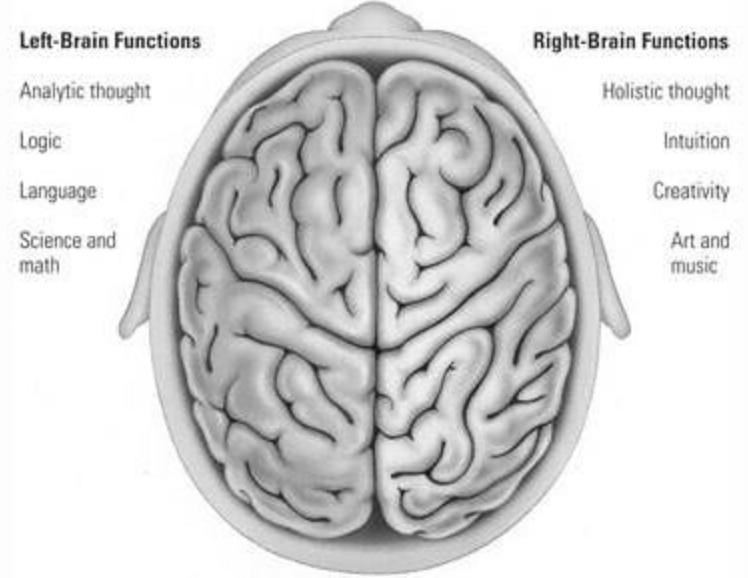隨著 2019年Netflix電影《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大獲好評,探討婚姻的電影再次掀起浪潮,其中一部再度引起關注的便是堪稱婚姻電影經典的《克拉瑪對克拉瑪》(Kramer vs. Kramer, 1979),由好萊塢兩大巨星達斯汀霍夫曼和梅莉史翠普飾演夫妻,劇情一開始直接從Joanna因為受夠丈夫Ted長期因為工作晚歸忽略家庭,使她獨自承受苦悶封閉的家庭照護之責,因此她毫無預警地留下小孩離家去追求自我,讓Ted一夕之間變成單親爸爸…。
然而,這樣一部描繪現代男女的電影,我看完卻覺得很不對勁,甚至是不太喜歡,因為《克拉瑪對克拉瑪》與其說是在探討婚姻裡的男女關係,我更覺得電影把鎂光燈照射在「男人帶小孩」這件事上。在電影裡我察覺到厭女的氛圍,厭女之餘這部作品還讚頌男人維繫家庭的偉大、男性照顧孩子的與眾不同,卻忽視妻子曾為家庭做出的犧牲,把女性自覺設定成離婚的因素,不去揭露男人在婚姻中曾犯的錯。
但這樣的想法我不敢確信,畢竟綜觀台灣影評圈皆讚揚這部電影的精彩,直到我最近讀到一本書《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在流行文化中被架空的社會運動》(WE WERE FEMINISTS ONCE: From Riot Grrrl to CoverGirl®,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 Political Movement),作者Andi Zeisler提出跟我相同的見解,我才終於不至自我懷疑是否觀影品味再度失準。
電影裡的性別偏誤
其實依據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上單親爸爸的佔比約是一到二成,而單親媽媽卻高達八成以上,但仔細想想我們很少見到電影去拍攝實際遭遇困境的這些多數——單親媽媽的故事,也沒有人去譴責無論何種原因(例如外遇)拋下家庭或自始未曾負起責任(射後不理)的孩子的爸爸們,《克拉瑪對克拉瑪》卻是將焦點放在不算多數的單親爸爸身上,Ted還是中產階級、經濟穩定無虞的一名角色,不禁令人質疑電影是否有意加深性別偏誤,也使觀眾誤以為單親爸爸是社會多數。
我記得在《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裡有一個我印象極深的一幕,金智英推著嬰兒車去咖啡店買杯咖啡時,小孩無法控制地哭鬧起來,立即引來旁人側目,眾人閒言閒語指責金智英沒做好媽媽該做的職責,並說著“現在家庭主婦怎麼可以那麼閒”可以跑出來買咖啡等語,不過當智英的丈夫(孔劉飾)為減輕妻子的負擔幫忙帶小孩出門溜搭時,旁人則是馬上為他貼上「好男人」的稱號,讚揚他貼心之舉。
這反映出父權社會把女性照護小孩視為理所當然,用非常嚴格的標準去檢視母親的一舉一動,失職了會被罵,照顧得好也不會被稱讚,對家庭中的父親角色,社會大眾給的是無盡的體貼與包容,不花時間與小孩交流天經地義,因他的責任在賺錢養家,但當他脫離社會的刻板印象去照護小孩時,受到的是與女性照護小孩時截然不同的正面評價,這就是我在《克拉瑪對克拉瑪》中看見的景象。
不難發現電影全心全意在營造達斯汀霍夫曼的「好爸爸」形象,在妻子離開後,他的事業與小孩兩頭燒,為了小孩他的工作表現越來越失常,因而讓他失去工作,透過讓觀眾看到男方的犧牲,打造丈夫的聖人形象,可是別忘了電影一開頭從妻子的離去開場,沒拍到丈夫過往對這個家所造成的傷害,顯然是有意忽略Ted作為丈夫的污點;反之,這樣的開場亦刻意不讓觀眾看見妻子Joanna曾經為家庭做出的犧牲,諸如:家庭主婦不能去做有薪工作讓自己經濟獨立,在家庭這個封閉環境長期負責照護,尤其她與丈夫欠缺溝通對話與理解,無人傾訴,其煩悶足以壓垮女人的精神狀態(這與是否愛小孩無關),而她的未來除了家庭,沒有任何發展性…但電影不管這些,梅莉史翠普在戲裡除開場與最後官司、結局外,是一直缺席的。換言之,男方戲份皆在呈現他與小孩共處的溫馨,女方唯有事業有成回來找小孩時才有戲份,不免給人負面觀感,這種手法將會給觀眾一個印象是,造成婚姻破碎的因素不是男人對家庭的忽視,而是女人追求自我的行為。
同樣是追求自我,丈夫拼事業、喝酒應酬,下班後無後顧之憂地享受休閒活動,假日依舊把家事丟給女人處理,自己跑去打高爾夫、看球賽等等,無人置喙;當女人厭倦長期無薪的家庭勞動,總算要抒展自己的手腳,離開家喘口氣,去追求自我、尋求一份工作,明明並非作奸犯科,此舉竟是被扣上「自私」的大帽子(Joanna回來爭取監護權更是加強這個形象),這點在電影裡不但透過監護權官司中男方律師咄咄逼人的言詞呈現出來,在男女主角在咖啡廳談判的那場戲,為表達憤怒的達斯汀霍夫曼,甚至脫離腳本即興演出,把玻璃水杯扔向梅姨身後的那道牆,碎成一地,誇張的情緒表現似乎也有意引導觀眾的仇女情緒。
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反挫浪潮撲向影視文化
《克拉瑪對克拉瑪》的誕生絕非偶然,注意它的出品時間是準備邁入1980年代之際的1979年,而1970年代是第二波女權運動崛起之時,象徵女性身體自主權一大進展的羅訴韋德案(註:2022年已被推翻)在這個年代誕生,與憲法《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的推動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也是在此時許多女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轉變,離婚率大幅成長。
但是第二波女權運動也面臨到所有社會少數權益推動時會遭遇的困境,越是進展,更會引起另一波比以往嚴重的保守反彈全面而來,1980年代共和黨候選人雷根的當選,正反映了意圖懲罰女權運動的美國民心,雷根上台後無所不用其極掃蕩他眼裡的「女權遺毒」,反墮胎、反平權、與宗教團體靠攏。此外,媒體早在政黨輪替前就開始抹黑女權,所謂男人出門賺錢養家、女人乖乖在家當家庭主婦的「家庭價值」風潮再度掀起,這股風也吹進了影視產業,《克拉瑪對克拉瑪》就首先開出了第一槍。前文提到的書籍作者Andi Zeisler如此描述:
後女性主義流行文化在描繪思想解放的女性時可是毫不含糊,她們不是邪惡地結合性自主及情感需求把男人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的心機潑婦,不然就是自身野心的瘋癲受害者。舉例來說,《克拉瑪對克拉瑪》中,自私的喬安娜必須「尋回自我」,於是丟下倒霉的丈夫獨自扶養她以往極少與之互動的孩子。
在1980年代左右產製的大量影視中,很多都會讓選擇工作而放棄傳統家庭角色的女人付出代價,《克拉瑪對克拉瑪》結局最後是Joanna自己放棄了孩子的監護權,似乎在傳遞著女人追求自我就無法兼顧家庭,其付出的代價是給出孩子,我很擔心電影這種強大的媒體可能會在社會大眾腦海裡植入保守父權價值觀,它像是嘲著女權運動宣揚的女性自主獨立哈哈大笑,諷刺女人選擇獨立所付出代價是自食惡果,賺錢養家的男人因為符合家庭價值而成為最大贏家。也許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只有男人可以兼顧自我與家庭,女人卻不能同時擁有兩者?再說,Joanna會來要小孩的行為,是不是在嘲諷女權主義者最終依然放不下家庭?
結語
事實上《克拉瑪對克拉瑪》不是全然只有缺點,它也一度要破除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那就是在官司進行中,Ted提出不應因為他是男性,就認為他沒有能力照顧小孩,亦即,他想打破男人總被認為不能勝任“母職”的偏見(法官傾向將監護權判給女性),這點我覺得非常好,畢竟在父權體制下,受到傷害的不會只有單一性別,男人同樣受到性別迷思所害。而電影某種程度的確是反映當時的社會景況,節節攀升的離婚數量,必然會產生一批單親爸爸,順應這樣的轉變,我們樂見一個大男人因為妻子的缺席、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增加,而日漸柔軟,體察到妻子過去家庭照護的艱辛。
《克拉瑪對克拉瑪》最初或許立意是良好的,但它問題出在電影的呈現手法、男女主角戲份差異、達斯汀霍夫曼那些節外生枝的暴力表演(還有一場戲無預警搧了梅姨耳光,畫面未曝光)均會引導觀眾的情緒導向妻子“很自私”拋家棄子的觀點,美化婚姻中的男人。
必須說我並不否認有單親爸爸的存在,不過我在意的點是,好萊塢缺乏真正社會多數遭遇困難的單親媽媽故事,當《克拉瑪對克拉瑪》選擇以佔少數的單親爸的角度出發,便是撇過頭不去看社會現實問題,單親家庭的產生不是女權崛起後才有,是父權社會長期以來對女性造成的持續影響,只是大家視而不見。單親媽媽帶兒找工作不易,為了兼顧育兒能找的多半也是低薪臨時工作,經濟狀況不穩定,這樣的女人不也很偉大,為什麼電影產業不去拍這樣的故事?第一,大家對單親媽媽的存在司空見慣,不感興趣;第二,單親爸爸比例偏少,足以製造話題,吸人眼球。
你會發現,即使有單親媽媽的電影,裡頭的單親母親通常是被醜化後的(例如有酗酒、吸毒、性生活荒淫無度、換過無數男友…)然後再想想那些單親父親電影,怎麼都父愛爆棚、毫無缺陷十分美好?好萊塢如此選擇性地呈現社會狀況,正是我所擔憂的,受眾是否有足夠智識去辨認大片廠構築的性別迷思?
觀看管道:Netflix
評分: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