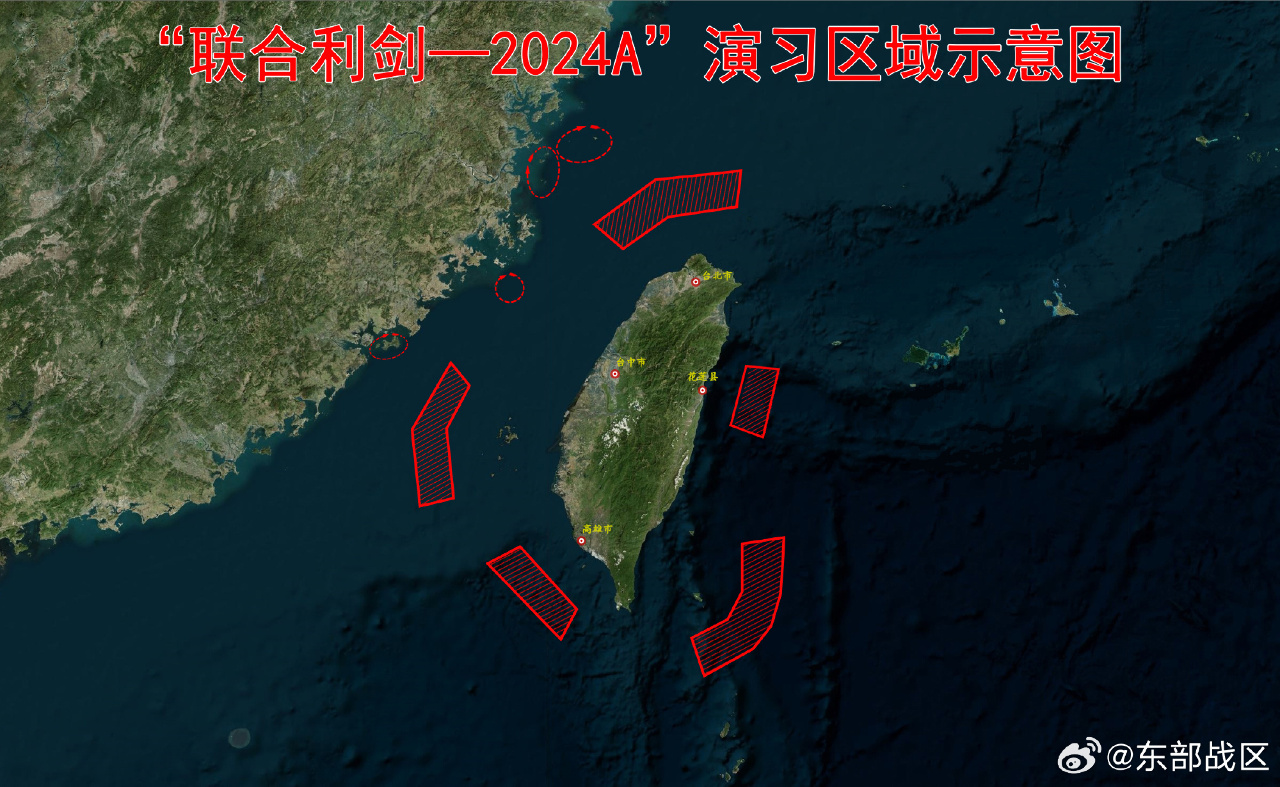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今年適逢《世界人權宣言》頒布70週年,各地都有盛大紀念活動,然而,再宏大的理想終究需要實踐;台灣人權從關注政治迫害到現階段將人權國內法化的落實,在一路傳承下,我們甚至看到1990年後出生的「九零後」擔起重任的身影,與早期社會運動者不同的是,他們是台灣解嚴後出生的一群,對街頭抗爭從小耳濡目染,甚至「躬逢其盛」四年前風起雲湧的318太陽花學運,這些社會運動留給「九零後」、四年前的大學生們什麼樣的記憶?他們如何在接下來的台灣人權運動中展現自己的姿態?
從陳雲林到太陽花 「九零後」抗爭中長大
走入位在台北市的一間小公寓,裡頭擠了7位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工作人員,1991年次的王曦,年紀最輕,也是唯一的九零後,台灣大學法律系與人類學系雙主修,課堂的啟發,再加上謀職當下的機緣,她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跟人權連在一塊兒。
台權會法務主任王曦說:『(原音)覺得自己會做這份工作好像還蠻合理的,因為很多人會說看事情的時候不要只看個人要看結構,好像我很自然會被推到看結構那邊,因為我們會很常需要倡議制度的改革,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很符合這個想法。』
王曦,現職是台權會法務主任,談起大五那年,離學校不遠的那場學運,她回憶,當時學校充斥罷課的氛圍,自己拿了本書就往現場跑,斷斷續續地與身旁互不認識的年輕人,靜坐近一個月。
王曦說:『(原音)那時候世界好像有種很動盪的氣氛,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剛好看到在青島東路的牆壁上,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這幾個字噴漆的當下,我目睹了那個時刻。』
當年這場社會運動爆發,撼動了台灣近年的發展,但王曦說,自己不算社會運動活躍者,更貼切地說,應該僅是一名旁觀者,就如同高三那年,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學校因為臨近總統府,周邊道路被封鎖後,她只能默默繞路而行,內心的疑惑與不滿都被龐大的課業壓力掩没。
就是想做 當公益律師是從小的目標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法務主任梁丹妮說:『(原音)冤案開再審的時候,當事人就會來這裡敲一下,像擊鼓鳴冤。』
梁丹妮是另一個在人權組織工作的「九零後」,1992年次,比王曦小一歲,她工作的地點,有如古代擊鼓伸冤的第一線,只是,此處的現場不是衙門口而是冤獄平反協會。

2017年,丹妮進入冤獄平反協會擔任法務主任,當一名公益律師是她從小的志願,在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考上律師執照後,就在夢想中前行。
丹妮說:『(原音)我從國中的時候就想做公益律師,那時是很天真地想說,有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法律對待之類的,但是,其實仔細要問我,我當時是遇到什麼事件,我真的講不出來,我沒有遇到什麼事情,家裡面也沒有遇到什麼法律的問題,但我就要做這件事情。』
與台灣早期從事人權工作的前輩原因大不同,丹妮家裡不是受政治迫害,也没有為重大法律案件所苦,就是一個想改變不公義的念頭,她大學時期關注過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以及318學運,雖然跟王曦一樣也是觀察居多,但是,她認為,彼此有話說出來不要悶在心理,是促使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
丹妮說:『(原音)我是覺得在民主的過程當中,它可能就是會有一些起伏和衝撞,像318學運讓那些大人們覺得這是很暴力或者甚至有攻擊性的那種情緒行為,其實我覺得它可能在我們現有的法律是不合法的,但它可能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就是我覺得說,吵架總比不吵大家都OKOK OK那就過了都好,那是畢竟我們有來回,我們才知道你為什麼要吵?你為什麼不同意?我覺得不管怎麼樣,至少要想辦法知道一下人家在吵什麼吧?最少這些大人應該要知道,不然我們OK做下去了,後面反彈更大或影響更大的話,那要怎麼收拾。』
的確,有話就說,而這也是一種溝通!更是台灣現在自由的社會氛圍,無論王曦還是丹妮,他們出生在台灣解嚴數年後,被自由的空氣餵養長大,没有恐怖時代下的政治威脅,只要願意,隨時都可以從旁觀者成為街頭行動者。
看見不合理 陳情抗爭由我們挑大樑
這是拿著大聲公,在立法院前為《集會遊行法》修法抗爭的王曦,求學時期,曾經的「路人甲」,轉身一變成為帶領群眾爭取權力的要角,王曦說:『(原音)因為我覺得現代國家的模樣應該是憲法肯認某些權利,像言論自由和集遊權是最基本的,假設我們這種權利没有被確保,那之後要主張什麼事情都不用談了。』
《集會遊行法》的修法是王曦在台權會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們認為,政府應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刪除「禁制區」規定與警察「強制排除」應按比例原則進行,避免執法過當。

王曦說:『(原音)因為現在台灣集會遊行還是要申請許可,這是集遊法規定的,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規定禁制區,就是某些區域不可以進去抗議,然後還有就是警察在什麼狀況下可以把一個集會遊行排除掉,那基本上就是覺得,如果你想要排除掉一個遊行那就要按著國際人權公約走,既然我們已經簽了國際公約。』
今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台權會再次走上街頭,趕在立法院會期結束前,大聲疾呼應正視諸多法案一讀通過後仍被擱置的情況,當中除了集遊法外還有難民法。
王曦說:『(原音)難民的議題,可能一般台灣人都會覺得台灣沒有啊!因為以前比較多的是從中國跟西藏來的,只是這幾年的改變就是從其他地方來的人變多,有從非洲、中東來的國家變多;其實因為難民法本身它會牽扯到國家主權的問題,就會變成大家有很多的意見,然後被擱置下來,所以就會變成沒有人要懂它,然後又因為難民這件事很小眾、没有選票,所以變成政府沒什麼誘因來討論這事。』
透過創意儀式 讓人權裡的大事再現
若提到「小眾」,另一個議題是冤案!因為多數人認為,這絕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其實不然。
丹妮說:『(原音)我們最新的案子是黃明芳,它是竊盜案件,這個案件看來其實很小,因為一般人會覺得竊盜就是偷個東西而已嘛!那為什麼他會來喊冤?因為他就是沒有做那件事情,而且他在第一審的時候被判無罪,之後第二審被判有罪定讞,但他其實並沒有一個再確認他到底有沒有罪的過程,所以我們就決定受理這個案件。』
憑藉法律專業,丹妮目前在平冤協會負責接案,待案件確立後再由義務律師團接辦,她說,2018年至今,協會成立的案件就有150案,她說,與往年相比案量還算少,可見過去工作量的負荷有多大。

丹妮說:『(原音)綠燈是已經平反的,黃燈的是它在開再審,那紅燈的話是目前比較沒有下文的案件,我們會希望當事人自己來換,有一個儀式感。』
推開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大門,映入眼中的便是一幅巨大的台灣地圖,丹妮介紹著地圖標示的每一個名字就代表一個冤案,有的已救援成功,但有的仍待努力中。
鄭性澤案無罪 目睹教學人物平反震撼
聊到一年來的工作,她說,自己參與了曾被「死刑定讞」的鄭性澤平冤案的後期任務,過程中,看見法界義務律師為案件奔走,以及敬佩當事人的堅持。
丹妮說:『(原音)其實我覺得,能參與到鄭性澤最後一段,他出來確定無罪的這段日子,我覺得應該算很榮幸吧!因為他就是我們大學的教材之一,可以這麼說啦!應該是2013年還是2014年,邱顯智律師是他的辯護人之一,他其實要來我們學校演講,對是那時鄭性澤案件都是沒有什麼進展,他去年確定無罪,等於說我參與了歷史,就是有那一種感覺;但是其實我最敬佩的是當事人,因為他們要有那個耐心跟毅力,他們才有辦法走到現在。』
鄭性澤三個字,對丹妮而言不僅僅是一個新聞報導中的名字,被冤枉囚禁4322天後,2017年11月鄭性澤獲無罪平反,這個在求學期間曾被討論的案例就這樣「活生生」地在眼前出現;但她的工作没有結束,接下來,平冤持續關切的案件-謝志宏案也是疑點重重。
丹妮說:『(原音)這個案件裡也有一些問題,例如警方沒有把全部證據移交給檢察官,是他最一開始寫得一個類似自白的東西,但是他在那一份裡面並沒有承認自己有犯罪,但是,後面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後,他才改說我有做。』
寄明信片給死囚 「九零後」英語教學創意互動
死囚謝志宏,捲入2000年台南歸仁的雙屍命案,法院採信了一份有刑求疑雲的自白,判決謝志宏有罪,他於2010年死刑定讞;在今年發現新證物後,更讓案件有了不一樣的轉機,目前台灣許多人權團體正為他奔走,丹妮也是其中一員。
她說:『(原音)我們有一個活動是每天寫張明信片給他,主要就是想要跟他聊聊天,讓他知道我們在幹嘛!就像我,平常就會寫英文單字教學,然後有時候會考獄中的他,你知道這叫什麼字?我上次有講過唷!其實在監所裡面真的是很無聊很無趣,讓他有一個可以做的事也是比較好的;但當然也不是只有謝志宏有這樣的狀況,其他的受刑人他們也會需要一些排解,因為在監所裡面受刑人真的是太苦悶了,因為我們這裡來的案件都是已經定讞的案子,很多當事人會寫信來,也可以看到他們常來信問,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出來?』
人權工作遇挫折 有自己面對的姿態
「錢多、事少」絕對不會被套用在人權工作者身上,除此之外,王曦坦白地說,工作中還有「失敗」!很多事,努力後也不會有成果已是家常便飯。面對這些,初入社會的「九零後」能調適過來嗎?
王曦說:『(原音)我覺得就是心理建設吧!要不然每天都會很生氣,昨天我們在跟志工聊天時,他就問說你們怎麼能忍受一直失敗?我就說沒差,反正我們只要覺得每天失敗很正常就好啦!可能有些事情真的是暫時做不到的,大家就互相講垃圾話,不然就很痛苦。』
丹妮說:『(原音)挫折和無奈一定會有的,你無法想像為什麼跟呼吸一樣自然的事情我還要去解釋,就是有時候會這樣子想的,但是,你如果這樣想的話就完蛋了,事情就不用做了,我覺得跟律師的這個職業可能也有關係吧!就是你要把自己拉回來一點,就是即使它沒有進度,你也是要想辦法去做事,你做事總比在那裡說,哦!天哪!為什麼會這樣?好吧,你要去處理到問題的本身,去敲敲敲,看能不能把磚塊敲少一點。』
綜合而言,人權工作五味雜陳,除了要專業、也需要堅持,更要新思維,在年輕一代的努力下,他們讓人權不只有悲情,而是一種展現自己的姿態!
人權宣言70周年 普世價值仍需落實
今年是《世界人權宣言》發佈70周年,回顧七十年前,人類在經歷二戰種種非人道事跡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開始起草,這份具有普世價值的文件於聯合國大會1948年12月10日通過。
對「九零後」的人權工作者而言,它是一份古老宣言,但它在人權史上里程碑的意義無法抹滅,像是宣言中的第1條就明確談到,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
王曦說:『(原音)我們很常在廢死的議題上面受到攻擊,就是壞人為什麼要有人權?我覺得說人權這個保障跟這個人是不是人渣?爛不爛?没有關係,就算他是人渣很爛,可是重點是他還是人,總之是人類的話,就享有人權,但這件事好像在社會上很難被接受。』
丹妮說:『(原音)我對於世界人權宣言哪一條比較有感覺?我覺得說生而為人,它不應該是一個需要被特別關注的事情,因為就是你就是一個人,那你知道要去尊重一個人,你希望怎樣被對待,那大概就可以做到那些宣言說你應該要做到的事情,我自己是這麼覺得啦!但是現實社會中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樣子,所以我現在還在理解這個社會中,呵!』
理想與現實或許存在差距,同時這個距離也多少伴隨著挫折而來,但這群「九零後」則以自己的姿態來面對。
人權實踐 「九零後」:我的成就感來源
當然,在人權組織工作的不是只限於法律專長,林晏竹是平冤協會執行秘書,1993年出生,學的是美術設計,但也是協會運作的重要一員,問她為什麼來人權組織工作?她說,青春應該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留下痕跡。

晏竹說:『(原音)我這幾年剛好有在關注一些社會議題,所以想說自己的專長可以有一點社會實踐,可以說是有點天真或什麼都好,但對自己在社會上面會有一點點期待,那個期待並不是追求金錢或是地位的期待,而是我看到社會好像有一些問題,如果我可以參與一點點什麼,甚至雖然說我不是法律系,但好像可以在不同的專長裡面都可以找到一種社會實踐的方式,那個會有一點點成就感,我覺得對於年輕人來講,然後就是那個虛無縹緲成就感,然後我就進來了。』
《世界人權宣言》表述的是所有人類應享有的最基本權利,但是若没有實踐,它則僅僅是美麗詞藻堆疊的文字;讓普世價值「深根」,並將人權工作一棒一棒接下去,才有可能將台灣各個角落打造一個「美麗新世界」。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ti 中央廣播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