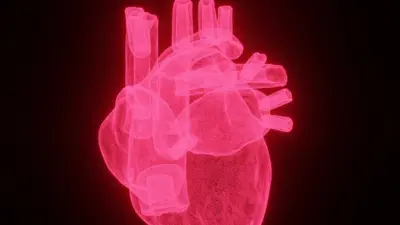印度小村莊禁止穿鞋的傳統從何而來
- 卡馬拉·泰嘉拉簡
- Kamala Thiagarajan

圖像來源,Kamala Thiagarajan
作為一個印度人,我對光腳的風俗習以為常。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了在踏進家門前把鞋脫掉(為了不把病菌帶到室內)。看望朋友和家人或是在印度教寺廟裏做禱告時也脫掉鞋子。即便習慣了這種風俗,但我對安達曼村的情況還是毫無心理凖備。

圖像來源,Kamala Thiagarajan
安達曼村位於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距離該邦首府金奈450公里(約7.5小時車程)。村裏住著大約130戶人家,多數人是在周圍稻田裏勞動的農業勞動者。
遇到70歲的阿魯穆加姆(Mukhan Arumugam)時,他正在村口一棵巨大的印度楝樹下做每天的禱告。他穿著白色的襯衫、方格子布的長袍,臉朝著天空。即使在1月底,這里正午的陽光也明亮得刺眼。
樹的旁邊是波光粼粼的地下水庫,周圍是油綠的稻田和鋪滿碎石的小路。他說:安達曼村的那個傳說正是從這棵樹下開始的。這裏也是村民進村前脫鞋,用手提著鞋開始赤腳走路的地方。
阿魯穆加姆告訴我:安達曼村除年老體弱者外,沒有人穿鞋。當時他自己也赤著腳,但他說,在即將到來的炎炎夏日裏,他打算開始穿涼鞋。當我穿著厚厚的黑襪子穿過村莊時,我驚訝地發現,匆匆趕往學校的少年和慢悠悠去上班的情侶,都滿不在乎地把自己的鞋子提在手裏。好像鞋子是個裝飾配件,就像錢包或包一樣。

圖像來源,Kamala Thiagarajan
我攔下赤腳騎車從我身旁經過的尼提(Anbu Nithi)。10歲的他在5公里外的一個小鎮上讀標凖五年級。當我問他是否違反過在村裏要光腳走路的規定時,他咧嘴笑了。他說:「媽媽告訴我,一位名叫穆塔亞拉瑪(Muthyalamma)的女神法力強大,保護著我們村,所以出於對她的尊重,我們這裏都不穿鞋。如果想穿,我也可以穿,但那就像侮辱一個大家都愛戴的朋友一樣。」
我很快發現,這種觀念讓安達曼村變得與眾不同。沒有人強制執行這種做法。也不是一條嚴格的宗教規定,只是一種飽含愛與尊重的古老習俗。
"我們是第四代堅持這種生活習俗的村民,"53歲的油漆匠潘迪(Karuppiah Pandey)解釋說。他手里正拿著鞋子,但他40歲的妻子,在田裏收割水稻的佩奇亞瑪(Pechiamma)稱,她根本懶得穿鞋,除非要去村子外面。她說,當有人穿著鞋去村裏時,他們會試著解釋這種風俗。如果對方不遵守,也不會有人強制執行。這完全是一種個人選擇,這種習俗得到過住在這裏所有人的支持。儘管她從未強迫過現已長大成人、在附近城市工作的四個孩子遵守這項規定,但他們每次進村來看她的時候,都會遵守這個習俗。

圖像來源,Kamala Thiagarajan
很早前有一段時間,人們不穿鞋是因為恐懼。
43歲的皮拉姆班(Subramaniam Piramban)是一名房屋油漆工,在安達曼村居住了半輩子。他說:「傳說如果不遵守這項規定,就會無緣由地發燒。但我們現在並不害怕這個預言,早已經習慣了把我們村當作一個神聖的地方。對我來說,它就像一座寺廟的延伸。」
為了弄清這個傳說的由來,我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村裏俗稱的歷史學家。在這個小村莊裏,62歲的維拉巴德拉(Lakshmanan Veerabadra)有著驚人的成功故事。40年前,他以日薪工人的身份出國務工。現在迪拜經營著一家建築公司,他經常回到村裏,有時候是為了招工,但主要是為了與家鄉保持聯繫。他說:據傳70年前,村民在村口的楝樹下豎起了一尊泥塑穆蒂亞拉姆瑪神像。就在神職人員用珠寶裝飾神像,人們在虔誠禱告時,一名年輕男子穿著鞋從神像邊走過。不知是否對儀式心懷不屑,但傳說他腳下一滑,摔倒在地。當天晚上突然發燒,過了好幾個月才康復。
維拉巴德拉說:從那時候起,村裏的人就不再穿鞋了,也由此演變成了一種生活習俗。村裏每5到8年,會在3月或4月舉辦一場慶典活動。活動期間,泥塑穆蒂亞拉姆瑪神像會被安放在楝樹下。神像會存留三天,為村子祈福。之後,神像被打碎,重新化為塵土。慶典活動期間,村子裏到處是禱告儀式、盛宴、舞蹈和戲劇演出。但由於花費很高,這種活動並不是每年都舉行。上次舉辦是2011年,下一次還不確定,具體取決於當地贊助者的捐款。

圖像來源,Kamala Thiagarajan
40歲的司機塞瓦甘(Ramesh Sevagan)說,這個傳說是安達曼村的凝聚核心,很多外村人認為這種傳說是迷信不予理會。他認為,這個傳說帶來了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它讓我們村子裏的人團結在一起,感覺村裏的每個人都像自已的家人。這種親近感又讓村裏延伸出另一種習俗。比如,村裏有人去世時,無論死者貧富,村民都會給失去親人的家庭送去數額不大的禮金,每人20盧比。既幫助了鄰居,也讓村民感覺無論順境還是逆境都有人陪在他們身邊,村子裏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想知道,時間、距離和國外經歷是否會淡化這種感覺。我問身在迪拜的維拉巴德拉,他現在對遵守禁鞋令是否還像小時候那麼堅持。他說是的,即使在今天,他在村子裏依然赤腳。過了這麼多年,他對遵循那個傳說的熱情並未消減。
他說:「不管是誰,生活在哪裏,我們每天早上醒來都希望自己越過越好,雖然無法保證,但仍為生活忙碌著。人們懷揣著夢想思考和規劃著未來。」
「每個地方的生活風俗中都蘊藏著簡單純樸的信念,只是你在我們村裏看到了另外一個版本。」
請訪問 BBC Cul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