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的問題:伯恩斯坦哈佛六講》:馬勒《第九號交響曲》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問題,還深刻揭示了一個答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伯恩斯坦是一位魅力四射、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更是美國首位躍上全球舞台的指揮家,在國際上享有巨星地位,同時是傑出的作曲家。這系列講座展示了伯恩斯坦廣泛的音樂興趣,讓人瞥見傳奇人物伯恩斯坦的仁慈、溫暖、智慧的光芒、精湛的演講能力和幽默感。「伯恩斯坦哈佛六講」是其職業生涯,以及調性音樂討論、大眾音樂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文:李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如果休息期間你眞的思考過了,此時腦子裡必定會有很多尖銳的問題。首先,為什麼是馬勒?馬勒和荀白克有什麼關聯?關係大著呢!首先早在二十世紀初,馬勒曾支持並鼓勵過的一位年輕同事,就是荀白克。但他與荀白克的關聯不僅如此。
再者,為什麼稱《第九號交響曲》是馬勒最後的遺囑?為什麼不是《第十號交響曲》,那部傑出的未完成之作?還有為什麼要用馬勒來結束一場以「二十世紀危機」為題的講座?這不是走回頭路嗎?我們已經隨著貝爾格和荀白克進入了二十世紀中葉,為什麼現在又要回到命運攸關的一九〇八年?
因為,正如艾伍士同年創作的《未解的問題》,馬勒的《第九號交響曲》也是一個偉大的問題,而且它不僅是個問題,還深刻揭示了一個答案。我本來準備像往常一樣,在鋼琴上分析這部作品,深入探索導致馬勒分裂的二元性——既是作曲家又是指揮家,既是基督教徒又是猶太人,既世故又天眞,既偏於一隅又面向世界。這一切導致其音樂組合呈現出精神分裂般的動態,以及馬勒本人對於調性十分矛盾的態度。
我也設想過,通過詳細分析他對倚音的處理,來觸及調性危機的本質;通過審視其「懸而未決」的緊張感,以及他嘗試捨棄調性時那種心不甘情不願的糾結——為我們進一步解釋之後荀白克與史特拉汶斯基之間不可避免的分裂提供相應的理論。
時隔若干年後,我再次拿起總譜,充分感受到馬勒的痛苦,因為他深知自己是那一脈的最後一人,自己是偉大的交響樂之弧的最後一段。這一圓弧發端於海頓、莫札特,在他這裡終結。我還意識到,一切註定要由馬勒來總結,用他回顧德奧音樂的整個歷程,對它打上一個結。這個結絕不是漂亮的蝴蝶結,而是馬勒拿自己的神經與肉身打的可怕死結。
當我重新研究這部作品,尤其是末段樂章的時候,我比預期得到更多答案。(每每重新研究一部偉大作品時,我們總會獲得新的東西。)其中有一個最驚人、最重要的答案,它闡明了從那時到今日整個世紀的主題:我們這個世紀是死亡的世紀,馬勒正是那個用音樂作預言的先知。我想與各位談談這個答案,捨棄鋼琴或視覺輔助,用一種不同於以往的交流形式。這部《第九號交響曲》給出了重要的語義解讀,一番無限寬廣的說明,吿訴我們所謂的二十世紀危機是什麼。
為什麼說我們這個世紀是前所未有的、被死亡纏身的世紀呢?難道這樣的說法放在別的世紀就不成立嗎?比如十九世紀,曾經以如此詩意的方式關注死亡。後有華格納的《愛之死》(Liebestod),前有濟慈的《夜鶯頌》(Nightingale),那一句——「我幾乎愛上了靜謐的死亡,用無數詩意的辭藻輕呼他名……」沒錯,從詩意和象徵性的角度而言,的確如此。所有世紀,整個人類歷史,不都是掙扎求生、面對死亡的漫長歷程嗎?是的,沒錯。但此前人類從未面臨過全球性的生存危機,沒有面臨過全面的死亡與整個種族的滅絕。
並非只有馬勒洞察到這一點,還有其他偉大的先知預見了我們的掙扎,包括佛洛伊德、愛因斯坦、馬克思在內皆有過預言,甚至斯賓格勒與維根斯坦,馬爾薩斯與瑞秋.卡森。所有這些人都是現當代的以賽亞和約翰,紛紛從各自的角度做著同一番佈道:「悔改吧,末日即將到來。」詩人里爾克也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二十世紀從一開始就是一部糟糕的戲劇,完全是古希臘戲劇的對立面。第一幕:貪婪和虛偽導致一場種族滅絕的世界大戰,戰後的不公正與歇斯底里,繁榮、暴跌、極權主義。第二幕:貪婪和虛偽導致一場種族滅絕的世界大戰,戰後的不公正與歇斯底里,繁榮、暴跌、極權主義。第三幕:貪婪和歇斯底里……我不要再往下講了。對策是什麼呢?邏輯實證主義、存在主義,科技高速發展,飛向外太空,懷疑現實:總而言之,是一種彬彬有禮的被迫害妄想症。
近來,這些症狀同樣表現在華盛頓特區身居高位的那群人身上。對於我們個體而言,又有哪些應對方式呢?大麻、亞文化、反主流,開啓潛意識、關閉潛意識,無所事事,擠出時間賺錢。一波新的宗教運動相繼湧現:拜古魯上師、拜比爾.格雷厄姆(Bill Grahamism)。另有一波新藝術運動,比如具象詩和約翰.凱吉的靜默。這裡才緩和了,那裡又整肅了。一切皆受制於死亡天使的股掌中。
假如你在一九〇八年就知道這一切,假如你像馬勒般極度敏銳,從直覺上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你會怎麼辦?你會做出預言,而其他人遵循你的道路。還有荀白克與史特拉汶斯基這兩位繼承馬勒衣缽的先知,儘管他們有著天壤之別,但都在相反的道路上奮鬥著,努力避免不幸的結局,保持音樂不斷持續地發展。實際上,本世紀所有眞正偉大的作品都誕生於絕望或抗爭,或是為逃避絕望或抗爭而建的避難所。這些音樂無一例外地被「痛苦」滲透。
想想沙特的《嘔吐》、卡繆的《異鄉人》、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太陽照常升起》、《魔山》、以及《浮士德》、《最後一個正直的人》,甚至《蘿莉塔》。另有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基里訶、達利等人的畫作;還有艾略特的《雞尾酒會》、《大教堂謀殺案》、《四重奏四首》,奧登的《焦慮的年代》,以及他創作生涯的巓峰之作——《暫時》(For the Time Being);還有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聶魯達、希薇亞.普拉斯。
銀幕上的傑作電影有《甜蜜的生活》,戲劇則有《等待果陀》。當然,還有《伍采克》、《璐璐》、《摩西與亞倫》,布萊希特的《勇氣媽媽》。沒錯,還有《艾蓮娜.瑞格碧》、《生命中的一天》、《她離家出走了》。這些也是誕生於絕望中,涉及到死亡的偉大作品。所有這一切,馬勒都預見到了。這就是為什麼他拼命拒絕進入二十世紀,這個死亡的年代,信仰的終點。苦澀而諷刺的是,他確實成功避開了這個世紀——一九一一年,正當盛年的他早早離開了人世。
玄妙的是,零散的拼圖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馬勒和他要說的話滲透在他接觸的每一樣事物裡。想想《悼亡兒之歌》(Kindertotenlieder),詩裡描述了呂克特的孩子的死,不久,馬勒自己的孩子也夭折了。而崇拜馬勒的阿班.貝爾格,把《伍采克》題獻給了馬勒的遺孀阿爾瑪,把《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阿爾瑪年輕美麗的女兒曼儂.格羅皮烏斯(Manon Gropius),這一切都沾染了死亡的氣息。
比如,我們剛才聽到的《小提琴協奏曲》是貝爾格生前最後的作品,寫於一九三五年。那一年他去世了,享年五十歲,恰巧與馬勒去世時的年紀一樣。諸如此類的巧合還有許多,但我們不要陷入超自然的神祕主義。這些事實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
貝爾格年輕時碰巧聽過馬勒《第九號交響曲》的演出,他隨即給在維也納的妻子去信,稱自己剛剛聽到了有生以來最偉大的音樂,諸如此類的話。我個人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共鳴。幾年前,我在馬勒當年所在的城市維也納演出他的作品。(馬勒的作品在當地被納粹禁演多年,那是第一次重新演出。)當時,貝爾格的遺孀也在,一位光彩奪目的老太太。每次排練,她總會到場旁觀,激動與欣喜全寫在臉上。我們就此相識。她成了活生生的見證與通往舊日時光的通道,帶我回到貝爾格、荀白克以及馬勒被死亡籠罩的瓜葛中。另一個見證者是阿爾瑪.馬勒,她在紐約參加了我的馬勒慶典演出排練。我開始感覺到,自己與馬勒要傳達的資訊有了直接的聯結。
如今,我們都已經知道馬勒要說什麼,他借《第九號交響曲》傳達了想說的話語。馬勒要說的是壞消息,然而當時的世界沒心思聽。這也是馬勒死後五十年裡,其音樂一直遭到忽視的眞正原因,而不是我們通常聽到的那些理由——太長、太難、太浮華云云。他的音樂說白了就是太眞實,傳達的東西太可怕,不忍卒聽。
到底是怎樣的消息?當時的馬勒看到了什麼?他看到了三種死亡。首先,他強烈感受到自己近在眼前的死亡。(《第九號交響曲》開篇幾個小節正是在模仿他的心律不整。)其次,他預見了調性的死亡,對他而言也就意味著他所熟悉和熱愛的音樂本身的死亡。他最後的作品既是在與生命吿別,也是與音樂吿別。想想《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最後的「吿別」(Abschied)好了。
還有備受爭議的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這部作品向荀白克式的未來跨出了嘗試性的一步,也有很多人嘗試續寫。即便如此,對我而言,《第十號交響曲》已然是一個圓滿的樂章,又一首讓人心碎的、訴說吿別的柔板,包含太多的吿別。我確信,馬勒永遠不可能寫完整部交響曲,即使他活下來也不行。早在《第九號交響曲》裡,他就已經把要說的都說盡了。
最後,他還預見到第三種死亡,亦是最重要的一種——社會的死亡,我們浮士德式文化(Faustian culture)的死亡。
既然馬勒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傳達得很淸楚,而我們自己也心知肚明,剩下的問題是,我們怎麼生存下來的呢?我們為什麼還在這裡掙扎前行?我們現在直面的是眞正終極的歧義性,即人的精神(human spirit)。這是最令人著迷的一種歧義性:正如我們每個人的成長,成熟的標誌便是學會接受死亡,但我們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永生。我們可以相信萬事轉瞬即逝,甚至萬事皆空,但我們依然相信有未來。我們就是有這樣的信仰。長達三小時的《甜蜜的生活》裡演盡了最卑鄙的墮落,但我們走出電影院後,依然能夠從純粹的電影創造力中取能量,擁有一雙翅膀,讓我們能夠飛向未來。
同樣的眞實還發生在劇院裡,目睹戈多的絕望後;或者是在音樂廳裡領受《春之祭》極富挑釁的暴烈後,甚至是聽完披頭四《左輪手槍》(Revolver)裡少年苦樂參半的憤世嫉俗以後,我們仍會生出翅膀。我們一定要相信那種創造力。我肯定相信。若是不信,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地做這些講座?肯定不是為了坐在這裡,公開宣吿世界末日。
我們內心,包括我的內心,一定存在某種力量驅使我們想要前行。我教書育人就是因為相信前行的力量。我與各位分享對過去的批判性感受,努力描述和評估當下,這些都隱含了對未來的堅定信心。
我希望這能夠解答前面那個問題,為什麼要用馬勒來結束一場關於荀白克的講座。因為荀白克是本世紀人類精神最偉大的代表之一,說到底,那種精神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他代表著「歧義的人」的原型:一邊不由自主地策劃著自我毀滅,一邊飛向未來。在下一講也就是最後一講裡,我們會發現史特拉汶斯基也是如此。整個「終極歧義性」都可以在馬勒《第九交響曲》最終樂章裡聽到,作品用聲音呈現了死亡本身。矛盾的是,每次聽到它又能帶來振奮人心的力量。
當各位聆聽這段終曲時,要嘗試著去瞭解在它之前發生了些什麼:三個巨型樂章,每一樂章都是一番吿別,各不相同。⋯⋯(中略)
直到這一刻,第四樂章登場,也是最後一個樂章——那個柔板,最後的吿別。⋯⋯(中略)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難以置信的最後一頁。我認為,所有藝術作品都比不上這一段落讓我們更接近死亡體驗,放棄一切的體驗。這一段慢到令人髮指,馬勒在樂譜上標注了「極慢板」(Adagissimo),音樂速度術語裡最慢的一種。似乎還嫌不夠,他又寫道:「Langsam」(慢)、「ersterbend」(消退)、「zögernd」(遲疑不決)。這些似乎依然不足以指示時間幾乎靜止的效果,馬勒在最後幾小節又添加上「äußerst langsam」(極慢)。非常可怖,彷彿被施了定身術,每一縷聲音都分崩離析。
我們牢牢抓住這一縷縷聲音,在希望與屈服間徘徊不定。這千絲萬縷的聲音讓我們與生命相通,現在它們一縷接著一縷地消散了。縱使我們奮力抓住,它們還是從指縫裡消失。它們化為無形的過程中,我們不願撒手。手裡還剩兩縷,然後一縷,一縷……突然全沒了。這凝固的瞬間,僅剩下沉寂。然後,又飄來一縷,斷裂的一縷,兩縷,一縷,沒了。我們幾乎愛上了安逸的死亡。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覺得死亡是一件奢侈的事,在夜深人靜時沒有痛苦地終結。終結之後,我們失去了一切。而馬勒的終結讓我們獲得了一切。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未解的問題:伯恩斯坦哈佛六講》,新經典文化出版
作者:李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譯者:莊加遜
- TAAZE讀冊生活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Pubu電子書城結帳時輸入TNL83,可享全站83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如實體、成人及指定優惠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史上最經典的六堂大師音樂課
20世紀古典樂巨匠 伯恩斯坦 思想精粹
哈佛大學諾頓講堂50周年完整紀念版
「教學一事,對我來說,是最根本的責任。從音樂獲取的知識與感受,我會全盤說出。」
——李奧納德・伯恩斯坦
奧斯卡7項大獎提名電影《大師風華:真愛樂章》(Maestro)傳奇人物
蘇打綠阿龔:
「樂音如話,樂譜如畫。
開篇第一首譜例就是我完成求學生涯的演奏及論文主題:科普蘭(Arron Copland)的《鋼琴變奏曲》,從音符發展出的藝術冒險就此展開。」
歷來最偉大指揮大師、思想巨匠、古典樂首位電視明星
音樂界全能代表、致力推廣音樂教育的伯恩斯坦 × 享譽世界的哈佛諾頓講座
貝多芬、馬勒協會獎章、紐約市最高文化獎Handel Medallion
16座葛萊美獎、7座艾美獎、2座東尼獎、甘迺迪中心榮譽獎得主
義大利、以色列、墨西哥、丹麥、德國、法國授予勳章表揚
從印度拉格音樂,到莫扎特、拉威爾,再到柯普蘭、荀白格、史特拉汶斯基,
伯恩斯坦考察全世界音樂創作的語法,包括民間音樂、流行歌曲、交響曲、調式、無調式、平均律作品,
以全新的觀點主張:無論是音樂或文學作品,都可回溯至一種普世語言,那是所有藝術創作的核心。
與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艾可《悠遊小說林》、《波赫士談詩論藝》齊名,
最受歡迎的諾頓講堂系列
美國古典音樂史上地位最高的指揮家、兼知名作曲家的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71年應哈佛大學邀請,舉辦六場哈佛諾頓講座。他以美國現代作曲家艾伍士(Charles Ives)的知名無調性作品《未作回答的問題》作為這一系列講座的標題,嘗試總結當時音樂史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音列主義和調性音樂之爭、古典音樂日後又該何去何從?
前三場講座,伯恩斯坦巧妙運用語言學家杭士基著作《語言與心智》,以語言學中的聲韻、句法,語義學,分析古典樂的聲音、結構與含義。
第四講,伯恩斯坦探討浪漫時期的音樂,其中和聲和樂曲結構更為多樣和自由。第五場講座「二十世紀的危機」概述古典樂朝向非調性發展的趨勢,這一重大變革是否將帶來危機?最後一場講座「大地之詩」聚焦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伯恩斯坦認為他已從中找到「未解的問題」可能的解答。
「音樂,是超越語言的語言,表達我們最深刻的情感與思想。」——李奧納德・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一位魅力四射、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更是美國首位躍上全球舞台的指揮家,在國際上享有巨星地位,同時是傑出的作曲家,創作出百老匯音樂劇《西城故事》、交響曲《焦慮的年代》、合唱樂曲《齊切斯特詩篇》、《岸上風雲》電影配樂等等。
這系列講座展示了伯恩斯坦廣泛的音樂興趣,讓人瞥見傳奇人物伯恩斯坦的仁慈、溫暖、智慧的光芒、精湛的演講能力和幽默感。「伯恩斯坦哈佛六講」是其職業生涯,以及調性音樂討論、大眾音樂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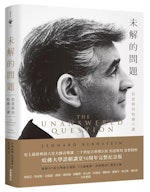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Tags:
立法院「國會改革法案」爭議引發群眾示威,BBC整理你該知道的五大關注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政治學者張峻豪則表示,這次立法院爭議涉及程序上公平正義的問題,觸及到許多年輕人和中間選民的神經,「不排除民進黨有動員,但是不能說這是執政黨帶起的運動」。他又認為,這次會否演變為「太陽花運動2.0」,現階段還是言之尚早。
文:李澄欣(BBC中文記者)

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台灣立法院「國會改革法案」攻防戰,繼上週發生激烈衝突後,週二(5月21日)恢復開會當天場外過萬民眾集結抗議,預計週五(5月24日)法案繼續審理時,示威會持續發酵。
有關法案最具爭議的是「藐視國會罪」,立法過程也被質疑違反程序正義,在野陣營以人數優勢「輾壓少數」。
這是年初台灣大選後立法院「三黨不過半」及「朝小野大」格局下發生的爭端,也是新上任的總統賴清德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外界關注未來台灣政治走勢,以及示威會否持續擴大演變成「太陽花運動2.0」。
有學者對《BBC中文》分析指,相比法案本身,這次爭議點在於審議過程的程序正當性,也有分析認為事件是大選後情緒的延續,反映了在野「藍白」陣營與執政「綠營」的撕裂,若雙方都不退讓,未來四年恐怕會繼續爭執不休,而北京樂見台灣亂局。
1. 國會改革法是什麼?
今年1月台灣大選選出113名國會立委,「藍營」國民黨、「綠營」民進黨、「白營」民眾黨分別獲得52、51、8個席次,構成國會「三黨不過半」格局,若在野的「藍白」陣營合作,可壓到執政綠營的人數。
這次爭議源於「藍白」共同提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5條修正條文,包括五大方向: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立法院調查權及聽證權、強化人事同意權、正副院長記名投票制,以及被認為最具爭議的「藐視國會罪」。
根據「藐視國會罪」內容,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的危害或依法應秘密的事項者並經主席同意者外,不得有「拒絕答覆、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訊、虛偽答覆」等藐視國會行為,違者經院會決議後可處新台幣2萬至20萬元罰鍰,逾期不改正可連續開罰。政府人員於立法院受質詢時,為虛偽陳述者,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此外,被質詢人不得「反質詢」,但未有明文定義何謂「反質詢」。
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認為,國會改革法案是要加強立法機關的監督能力,重點之一是政府官員不得在國會聽證備詢時說謊或蓄意隱匿,並強調歐美國家都有藐視國會罪,條文主要針對政府人員,普通民眾不會受到刑事處罰,且需經過法院宣判才能算數。

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民進黨則表示,藐視國會罪定義過於寬鬆,恐引起寒蟬效應,又質疑過分擴張立法院權力會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可能違憲。另外,部分商界憂慮條文衝擊營商環境,若私人企業被要求到立法院接受質詢,可能要交出投資計劃和商業機密等資料,否則被扣上藐視國會罪。
部分反對聲音的論點也包含對「中國因素」的憂慮,指推動法案的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傅崐萁,4月曾率領十多名黨籍立委訪問北京,會見大陸國台辦高層和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批評者擔心北京可能希望藍營為國會「擴權」,以降低民進黨行政當局的執政效率。
2. 立法過程為何引爆朝野衝突?
台灣立法院會議(簡稱院會)每週二、五舉行。根據立法流程,一個法案提出後會經過程序委員會確認,送到院會一讀,接著需要過三關:委員會審查、黨團協商、院會表決。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指出,這次爭議的關鍵,主要不是國會改革問題,而是黑箱作業、缺少討論、有失程序正當性的問題,另外是國會多數是否藉國會改革之名濫權。
「在民主體系下,行政、立法本來就有互相牽制的自然張力,問題是在野黨是否能夠及願意扮演忠實的反對角色,還是會利用權力來把持政府正常運作。」
回溯是次立法過程,大選後新一屆立法院在2月20日開議,3月份國民黨和民進黨先後提出國會改革法案,並交付司法法制委員會審查。該委員會中,民進黨委員有6人,國民黨及民眾黨委員有6人,而主席為國民黨召委吳宗憲。
民進黨版本經3次公聽會及委員會逐條審查後未被納入,國民黨版本則在4月15日進入委員會逐條審查,主席聽到「有異議」便宣佈「保留」,民進黨委員則於每條「保留」後動議散會共計40次。「藍白」黨團在7比6的人數優勢下,把沒有共識的所有條文「保留」並送出委員會,提交黨團協商。
經過一個月的法案「冷凍期」後,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在5月16日召集朝野協商,在長達六小時的會議,藍綠不歡而散,未觸及國會改革法案條文,就送交院會。
5月17日,藍白兩黨以修正動議方式提出國會改革修法的「整併版本」,要在院會二讀表決,民進黨為阻止會議進行佔領主席台,朝野雙方爆發多輪激烈肢體衝突,六名立委受傷送醫,包括民進黨立委沈伯洋、邱志偉、莊瑞雄、鍾佳濱、郭國文,以及國民黨立委吳宗憲。
民進黨團質疑,表決時沒看到藍白共提版本,是「未討論就表決」和「黑箱作業」,違反程序正義,形容是「國會人大化、香港化」。民眾黨黃國昌反駁指,議場內每個立委桌上都有修正動議、再修正動議,甚至在野黨也是坐在議場內才看到民進黨團提出的80個表決版本。
3. 三黨如何表態?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表示,呼籲在野黨「尊重少數」,審慎思考相關法案對現行憲政體系所造成的影響。他說遵守程序正義的實質、理性討論,是民主法治國家國會的原則,也是各黨可以達成共識的關鍵,缺乏程序和實質討論,會讓法條難以凝聚各方共識,容易產生疏漏,甚至可能影響現行憲政與權力分立的運作。

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表示,國會改革是朝野各黨數十年來的共同主張,也是前總統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時曾經提出的,他呼籲民進黨「別想再以少數輾壓多數,用拳頭取代數人頭,以街頭壓制國會」,稱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若引起民主內戰絕非台灣之福。他又批評,民進黨不應以「抹紅」方式對待在野黨,應把國家利益放在政黨利益之上。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表示,國會改革法案的內容都是過去民進黨的主張,他呼籲執政黨不可以用傲慢態度背棄過去的理想,甚至用暴力方式阻礙,又說正所謂「當家不鬧事」,質疑為何執政黨會帶頭抗爭。他回應該黨為何與國民黨合作時稱,選後至今總統賴清德陣營沒有任何人與民眾黨溝通接觸,「民進黨都把我們列為拒絕往來戶」。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張峻豪教授對《BBC中文》形容,這次事件是大選後一種情緒的延續,反映了「藍白對於綠營的仇恨感,街頭民眾對於藍白的仇恨感」。但他指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藍白滿意度不斷下降,主流民意還是不想看到國會爭吵打架的亂象,藍白政黨將要多做評估。
他提到,5月20日新任總統賴清德就職之前,立法院針對的是看守政府,5月20日之後則面對新的行政機關,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未來要看「關鍵少數」的民眾黨要繼續跟著國民黨走,還是轉為與民進黨合作。「新的政府上台之後,有很多行政資源分配的空間,賴清德有很多可操作空間。又譬如說民進黨提出青年政策,那民眾黨要不要合作?」
至於事件將如何影響新上任的賴清德政府?學者莊嘉穎表示,這次抗爭主要針對國會濫權,與賴清德政府沒有很直接的衝突,只要賴能維持秩序,適當地運用民意,或許一方面可以制止國民黨和民眾黨,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個人支持度。
「但前提是他必須鎮得住腳,恰當地回應民意,不能超過適當的範圍——要是顯得借用民意刻意報復國民黨、民眾黨和削弱國會權力,在民眾眼中就會有些過分,因為這樣跟藍白現在濫用國會權力差不多。較為適當的做法,是藉機會釐清分權和民主體制,尤其是行政、立法、司法的部分。」
4. 會否演變為「太陽花2.0」?
5月21日,民間團體號召民眾集會抗議,下班下課時間後,立法院外的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口、忠孝東路持續湧入大批人潮,主辦單位之一「經濟民主連合」宣佈現場聚集人數超過三萬人。
現場民眾在雨中手持「我藐視國會」、「反黑箱,反擴權」等標語,高喊「沒有討論,沒有民主」的口號,亦有人們手持太陽花。
台灣晶片業大亨曹興誠也出席集會,他上台分享指「擴權法案是把立法權壓著行政權,壓著司法權,最後變成立法獨大」,這樣的話將來立法院可以指揮行政院、司法院、警察及軍隊,他又稱中國正在把台灣的立法院變成香港的立法會,表示台灣不要變成香港。
美國德州的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對《BBC中文》表示,社會運動此時爆發,對執政黨而言還不知是福是禍,假如事件升級為「太陽花運動2.0」,群眾衝撞立院,對執政黨的挑戰不會小,「恐怕連美國也會重新思考如何評價,因為當家的執政黨作亂,對於民主國家來說是很難想像的」。
政治學者張峻豪則表示,這次立法院爭議涉及程序上公平正義的問題,觸及到許多年輕人和中間選民的神經,「不排除民進黨有動員,但是不能說這是執政黨帶起的運動」。他又認為,這次會否演變為「太陽花運動2.0」,現階段還是言之尚早。
2014年3月18日爆發的「太陽花運動」,源於時任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在立法院用30秒時間,宣佈備受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已超過3個月審查期,應當視為「已通過」,過程被指黑箱作業,激起民憤,學生和社運人士佔領立法院長達23天。
5. 北京怎麼看?
中國政府沒有就台灣立法院爭議表態,但在賴清德上台後,北京以強硬口吻警告台獨是「死路」,批評賴清德就職演說「充斥著敵意與挑釁」,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台獨自白」。而在他就任僅僅三天,解放軍就「無預警」地進行環台軍演。
學者莊嘉穎表示,北京很希望給賴清德政府和民進黨下馬威,指中共有滲透的前例,不能排除他們會激化台灣內部分裂,更能讓他們對台施壓,設法延伸控制。張峻豪教授也指,北京樂見台灣亂局,「島內」越亂,中共的操作空間越大。
翁履中認為,在國會改革法案爭議上,假如藍綠雙方互不妥協,進一步兩極化,未來四年恐怕就是如此的爭執不休,長遠會影響台灣安全,「真正要擔心的是,台灣不團結對未來國家安全策略和方向造成衝擊」。
本文經《BBC News 中文》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延伸閱讀
- 場外罷免韓國瑜,場內拜託韓國瑜:524再戰國會改革法案,有可能成為「太陽花2.0」嗎?
- 《日經亞洲》:國會職權修法為何爭議如此大?是否影響台灣抵禦中國威脅?5大重點一次看
- 立院24日續審國會職權修法:綠擬文攻、藍嚴陣以待,400警維安待命,全台7縣市「我藐視國會」串聯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