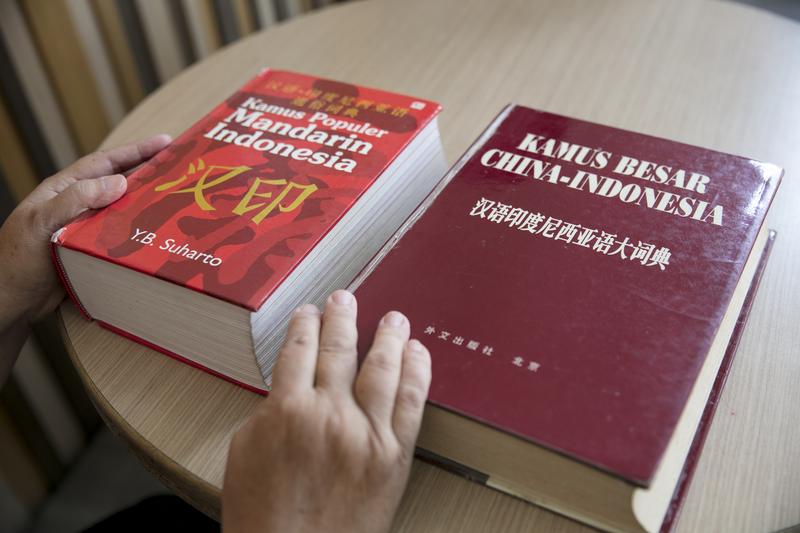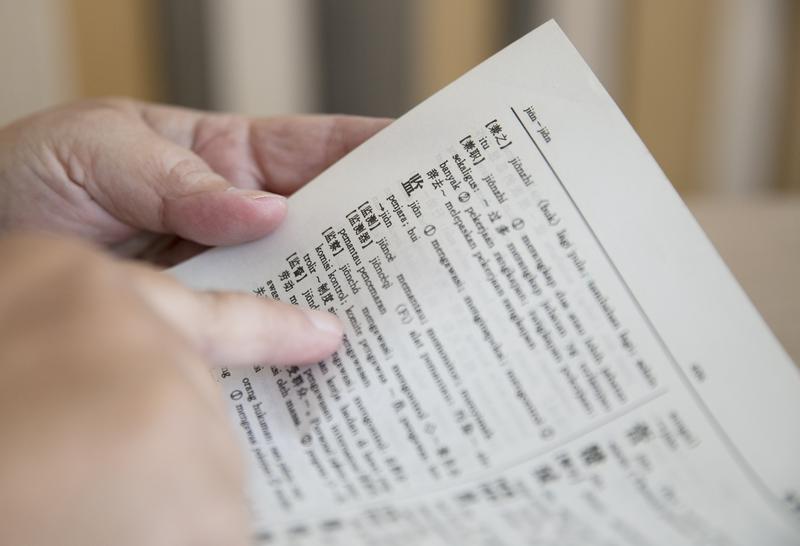聆聽,是為了理解

口譯員在各種場合中搭起溝通橋梁,自己卻往往是隱身的角色,一般人也鮮少有機會認識口譯工作。但隨著直播流行,每當有政治和外交等重大事件發生,居中服務的口譯員也開始受到關注。無論外界對口譯表現是褒是貶,評價的標準是否合理?當新聞充斥著「口譯哥」、「口譯妹」等空泛標籤,整個社會又將如何理解口譯專業?
「你看,我自己也有帶口罩啊,我這裡也有準備口罩啊,我需要的時候我會戴啊!」
幾乎同一時間,身處太平洋另一端的台灣口譯員鄒德平,也彷彿要從西裝上衣摸出什麼似的,一面做出相同手勢,一面不間斷地翻譯:「需要的時候我會戴口罩,我不會像他(拜登)一樣,就是到處都戴口罩啊!他就算離我200英尺,他還是會戴一個大大的口罩,他怕什麼?」
這是《中天電視》為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所做的實況轉播,畫面左下角和右下角各有一個方框,讓觀眾清楚看見兩位口譯員。其中,負責翻譯川普的鄒德平不僅譯文精準流暢,連川普揮舞的雙手、嗤笑的口吻都模仿得唯妙唯肖,被同業戲稱為「台灣川普代言人」。

鄒德平畢業於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從2014年開始擔任自由接案的口譯員,平時相當關注美國政治。2016年,他在《中視》的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轉播中擔任口譯,也為《寰宇新聞台》翻譯川普的總統勝選演講,2017年為《TVBS》翻譯美國總統就職典禮,2020年受到《中天電視》委託,在兩場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的實況轉播中翻譯川普發言。2023年起,當《美國之音》(VOA)轉播一系列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聽證會,鄒德平也受託擔任同步口譯。
在大多數會議或論壇上,口譯員總是默默隱身在口譯廂裡,但媒體直播多了表演性質,口譯員除了傳遞訊息以外,有時還要協助節目進行、回應觀眾期待,可以說是身兼多職,音訊環境卻不如普通會議穩定,若口譯內容涉及政治和外交等茲事體大的領域,壓力更是排山倒海。
鄒德平曾獲第四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二等獎,在該年的台灣參賽者之中是排行最佳的選手,具備良好的台風和應變能力,能夠勝任電視口譯並不令人訝異。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工作機會光是用想像的,就讓他躊躇不前:
「我目前接的都是美國的,某方面來講可能我的風險沒那麼高,台灣人對於美國政治比較不會這麼激烈,但如果是要我去幫民進黨或國民黨或民眾黨口譯,而且是公開場合的話,我可能會三思。」
鄒德平解釋,口譯員在政治場合經常遭到放大檢視,有時甚至會因主辦單位的瑕疵而背上黑鍋,承受種種無法控制的後續效應,「我覺得這種政治場合的譯者,真的要有一種『為國捐軀』的領悟耶!」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這番感嘆聽來誇張,但包括執業已20、30年的資深口譯員在內,不少口譯員近期受訪時都透露類似的心情,原因是口譯工作原本就風險重重,影響表現的變數很多,外界卻不一定了解。近年來,網路直播的盛行更放大了這種風險,而部分媒體對口譯員所做的報導,以及社會大眾評斷口譯員的方式,都在在加深他們的顧慮。
其中一個經典案例,就是2022年的「裴洛西事件」。

2022年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旋風式造訪台灣,隔日赴立法院與副院長蔡其昌會談。該場會談安排兩位口譯員,分別坐在裴洛西和蔡其昌斜後方做逐步口譯,亦即講者說一段話、口譯員翻一段話,如此來回交替。
由於裴洛西此行意義非凡,象徵著台美關係25年來的重大突破,媒體紛紛在YouTube頻道開設直播,過程中,為裴洛西翻譯的口譯員因數度打斷裴洛西與笑出聲,遭網友批評「沒禮貌」、「沒水準」,事後也成為眾多媒體報導的焦點,被質疑有損專業與國家形象。
在一片殺伐聲中,口譯界呈現截然不同的風景。有身經百戰的資深口譯員在個人Facebook為事件主角抱屈,直言即使是自己也不一定能表現更好。有碩士生針對這起事件展開研究,彙整過往的翻譯學文獻、多位口譯員的實務見解,最後凝聚出有別於輿論的分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該研究顯示,多數受訪者都認為「能否打斷講者」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原因是「講者講太多、太長,導致負荷量太大、訊息不完整,或是沒有發揮溝通的功能,才是不專業的」,只是要在何時、用何種方式打斷尚有討論空間。有人更提醒,需要口譯的人除了講者以外,還有媒體和網路上的觀眾,口譯員若要善盡溝通的職責,有時甚至是「必須」打斷講者。
至於不小心搶話的狀況,一位在政府機關任職7年的口譯員觀察到,由於該場會談的座位安排以及大家都戴著口罩,口譯員恐怕較難從表情和肢體動作判斷講者是否已經講到一個段落,輪到自己開口。
所謂的打斷講者有三次,第一次發生在口譯員翻譯到一半、工作人員前來更換故障的麥克風時,裴洛西疑似誤會翻譯已經結束,拿起麥克風要繼續致詞,口譯員匆匆攔住她的話頭,輕聲解釋剛才只是在換麥克風,隨即繼續完成剩餘的翻譯。第二次是口譯員打斷裴洛西講到一半的句子,輕聲說明要先翻譯,同時向裴洛西致歉與道謝。第三次是裴洛西講完一個語意完足的句子後,停頓兩秒又再度開口,一瞬間與正開始翻譯的口譯員聲音重疊,而口譯員說“sorry”後立刻斂聲,讓裴洛西繼續致詞。
另外,當裴洛西提到美國議員金安迪(Andy Kim)的外交官背景,說“so he's teaching us to speak more diplomatically”(所以他在教我們講話更圓滑),口譯員首次笑出聲音;當裴洛西提及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說“she told me just to address her as Sandra”(她要我直呼她珊卓就好),口譯員第二次笑出聲音;當裴洛西以輕快語氣說“I think we're right on time”(我想我們時間剛好),口譯員第三次笑出聲音並開始翻譯,替致詞畫下句點。其中,口譯員第一次和第三次發笑時,現場也傳出笑聲。
口譯員發出笑聲是否合乎專業?該論文的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只要場合是歡樂的,且在場其他人都在笑,口譯員沒有不能笑的道理;有人更指出,在適當的場合笑反而是更自然的表現,代表口譯員也融入講者所營造的氛圍與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這8位論文受訪者有何見解,他們在評論裴洛西的口譯員是否專業時,通常會提出具體證據,也並非仰賴單一指標。例如有人指出,該位口譯員將訪團成員的背景和法案名稱翻譯得非常完整,可見事前準備相當充分。而儘管H不認同該位口譯員打斷講者和發笑的表現,然而當H依照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舉辦過的「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為其評分時,仍然在譯文準確度和表達流暢度兩方面,在0~5級分之間給出4級分的評價。
綜觀楊心語的研究,也可以發現網友和多位口譯員的意見之所以有落差,與他們如何想像口譯員的定位有關。口譯員究竟只是「傳聲筒」、「翻譯機」,抑或擁有較大的自主性,能根據自己認定的需求做出判斷?
這個問題沒有一體適用的答案,但目前已知的事實是,口譯員的功能常常不僅限於翻譯,有時還會適時緩和或帶動現場氣氛,或以其他方式因應情境、確保溝通順利進行,從政治、外交領域到社區口譯中的醫療場合都有這類案例,而這向來也是國內外翻譯文獻探討的一大重點。
舉例而言,由3位香港學者發表的“Interpreter visibility in press conferences: a multimodal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peaker–interpreter interactions”(〈記者會中的口譯員能見度:講者與口譯員互動的多模式對話分析〉)一文,分析了美國在台協會召開的8場記者會,發現講者平均每5分多鐘就會提及口譯員及其譯文一次,包括讚美口譯員的表現、糾正小失誤並拍肩安慰,或提醒口譯員要喝水,而口譯員偶爾也與講者一搭一唱地開玩笑,合力營造輕鬆愉快的記者會。英國教授安潔樂莉(Claudia Angelelli)則調查300多次醫院裡的口譯服務,在2004年發表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醫療口譯與跨文化溝通》)一書,探討醫療口譯員能如何積極主動地參與醫病溝通,而不是固守傳統定義下的「隱形」和「中立」身分。
儘管不同情境無法一概而論,但由此可知,口譯員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應該與講者有怎樣的互動,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可能。
然而,在2022年裴洛西會談的即時新聞裡,未能見到有關口譯的細緻思辨,許多媒體僅剪輯口譯員引發關注的片段反覆播送,並且為裴洛西添加「內心話」的字幕,讓她看起來充滿無奈和抱怨。以《三立新聞網》的〈麥克風故障!口譯妹4度打斷裴洛西還訕笑 網怒炸:不專業〉影音報導為例,除了運用上述製作手法,該則報導的描述也容易讓讀者誤判設備故障的責任歸屬,且根據台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定義,訕笑有「諷刺嘲笑」之意,但口譯員有兩次發笑時,立法院現場也同時傳出笑聲,在這種情況下,口譯員的笑聲是否獨獨帶有「諷刺嘲笑」的惡意,顯然還有待商榷。

當然,台灣媒體並不是永遠都在批判口譯員,有時也有正面的報導。但曾在2017年為台北市長柯文哲翻譯,因而受到媒體和網友一致好評的口譯員郭恬君,對於種種「讚美」也並不領情:
「我覺得大部分時候,我們上新聞都不是因為大家真的想要討論口譯怎麼樣,而是因為其他的原因,所以把口譯這個角色也拿出來講一講,因為我們就是在鏡頭前面被拍到的那一個人⋯⋯不然他們為什麼只聽(柯文哲罵的)『王八蛋』三個字,其他部分都不聽了?如果是口譯同行,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一定是討論其他的部分,不會只有『王八蛋』這個部分。」
2017年8月19日,反年改團體赴世大運開幕會場外抗議,造成各國選手延後進場。作為主辦單位,台北市長柯文哲隔日召開記者會表示譴責,回應提問時更怒罵抗議人士是「王八蛋」,此話一出掀起熱議,在記者會上負責翻譯的郭恬君也隨之成為新聞話題。
事隔6年多,郭恬君分析說,這件事如果搬到2024年的今天,或許會招來不同的評價,她說不定也會遭受牽連,但柯文哲當年因「敢言」形象受到歡迎,又在如此重大的場合罵出「王八蛋」三字,「大家就會覺得很爽啊,會覺得很開心啊──柯市長用中文罵了王八蛋,然後還有一個口譯來幫他用英文『再罵一次』。」
郭恬君表示,當她意識到這件事有炒作空間,她立刻聯繫世大運翻譯團隊,請負責人替她拒絕採訪,「他們(媒體)絕對不是關心口譯,是需要做更多花邊新聞。我不想要成為這個花邊新聞的一部分,因為我覺得這個沒什麼意義,我也不可能在這時解釋關於口譯重要的訊息。」
回顧當時提到口譯員的新聞,可以發現她的判斷非常準確。《中視》的〈網友臉書嗆“誰是王八蛋”!柯P神回:就是你〉,形容郭恬君「長髮大眼、甜美笑容」,讓網友有戀愛的感覺;《東森新聞》的〈王八蛋翻成英文!柯文哲口譯憋笑完成工作〉,描述她「嘴角曲線微微上揚,融化網友的心」;《三立新聞網》的〈柯怒罵王八蛋 女翻譯靦腆憋笑超吸睛〉為郭恬君和議員高嘉瑜製作對照圖,因為有網友說她們長得很像⋯⋯。
對女性品頭論足是媒體長期以來的弊病,談及此事,郭恬君更舉出男性口譯員上新聞的例子表示,他們就算是被批評,通常也不會涉及性別,不會像裴洛西的口譯員那樣被稱作「口譯妹」,「我不知道欸,男生有什麼貶低性的(用語)?」
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或郭恬君究竟是否神似高嘉瑜,能夠確定的是,在柯文哲記者會的新聞狂潮中,觀眾失去了深入認識口譯工作的機會──儘管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能說明口譯工作的高壓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事出突然。在記者會開始的一個半小時前,郭恬君才接獲委託,於是她立刻開始爬梳反年改團體陳抗事件的相關新聞、預測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查詢用得到的詞彙。至於柯文哲的4項聲明,她幾乎是記者會開始前的最後一刻才取得,而且沒有紙本,「我其實是看著我手機上一個有點模糊的照片,在翻那個聲明稿。」
這種看著文稿,當場把內容口譯出來的模式,稱為「視譯」(sight translation),是專業口譯訓練中必備的一環。口譯員要眼耳兼用,一邊根據文稿來翻譯,一邊留意講者是否脫離文稿即興發言、提及的資訊跟文稿有無出入,若有意義上的明確落差,就必須放棄文稿專心聽譯。
當高階官員等講者在正式場合致詞,通常會擬好講稿,上台時直接念稿,但書面文稿去除了冗言贅字、停頓、呼吸等特點,變得異常精煉,講者在念稿時也經常忽略觀眾反應,流於快速宣讀。
由於口譯工作主要是處理自然的言談,面對訊息密度過高且飛快的表達方式,口譯的精準度可能會略為下降。然而,正式場合格外需要精準和完整的訊息,因此,若口譯員能提前拿到原文講稿,就能提早準備,以確保翻譯的準確性和一致性。若該位講者及所屬組織有指定、習慣或偏好的用語,有時也會提供翻譯好的稿件,要求口譯員以此為本。
但儘管有稿件作為參考,受過專業訓練的口譯員仍會留意可能的脫稿,適時修改及補充資訊。結論是,口譯員若沒有拿到講稿,仍然可以完成翻譯,但有稿可以讓翻譯更加精確、符合講者的溝通意圖。
郭恬君畢業於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口譯組,曾通過台師大及輔仁大學合辦的中英口譯聯合專業考試,也曾獲得第二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冠軍,基本功非常扎實,抗壓性也非比常人,在記者會上沉穩化解各種挑戰。真正讓她困擾的,是口譯員最重視的「音質」:
「我跟他(柯文哲)坐的位置,是中間又隔了一個空位,然後那個場地其實也滿大的,現場有非常多的媒體。當然,人多就是會有很多的雜音,可能是筆記的聲音、紙的聲音,可能是攝影機的聲音等等⋯⋯他講話的內容,其實我是要很吃力地聽,才能夠聽到。」
音質不佳,對口譯員來說是存亡攸關的危機。郭恬君憶及,聽到「王八蛋」三個字迸出來時,她感到不太確定,直到下一秒,現場猛然炸開一陣快門聲,她才相信自己的耳朵。
同時,全場目光聚集到她身上。
「我不能選一個f-word,這個太過了⋯⋯那如果只是idiot這一種,好像也不夠強烈,因為王八蛋比『做蠢事』或是『蠢蛋』,好像又再更強烈一點,它真的是有一種辱罵的味道。」郭恬君說,她的腦海裡一瞬間跑過幾個選項,最後選擇了強度適中的“bastard”(混蛋)。
或許有人會問,作為口譯員,當我方官員在國際媒體前爆出粗話,到底要翻還是不翻?對此,郭恬君毫不猶豫地解釋,以柯文哲這場記者會而言,她從未考慮過不翻:
「無論他是失言,還是他是刻意而為,他都做了這件事情,而且這件事情是2,300萬人可以看到的、在媒體前面做的,它一定會有什麼意義,一定會有什麼效果⋯⋯無論他是刻意而為的一個人設,還是他真的就是這樣子的個性,這個不是我需要判斷的點。我需要判斷的就只有,以他這個人在當時那個場合,他講出這句話,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傳達這個意思?然後他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想要用這個字來傳達這個意思?」
此外,郭恬君在翻譯時也頻頻抬頭望向觀眾,而非埋頭閱讀筆記,「逐步口譯的時候,我其實就是講者之一嘛,我是『另外一個語言的講者』。對於任何在聽人家講話的人,他當然都希望你可以看著他,希望有一些視覺上的互動。一方面我也需要看到你現在到底有沒有聽懂──我是講得太快了,還是你覺得很不耐煩了。」
翻譯乍看只是語言轉換,實則包含許多層次的決策。然而,當這一切在新聞綜藝化的風潮下,只化約為「口譯哥」與「口譯妹」等標籤,再加上網路直播和社群媒體的發達,口譯員的毀譽僅繫於一個字、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這種現象就影響了許多人從事特定類型口譯的意願。

「之前如果你想要出頭,或建立自己的名聲,最好的方式就是做這些high-profile(備受關注)的會,但現在完全是沒那麼容易,除非你很有把握能夠做得很好。總統府那些記者會都會直播,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所有人都可以批評,他只要錄下來一句一句地去批評,你百口莫辯。」
帶著一絲沉重,口譯資歷逾25年的徐子超分享他從業至今的心聲。
早在千禧年以前,徐子超就開始從事口譯,日後陸續經歷了許多鎂光燈聚集的場合,曾擔任籃球明星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柯比.布萊恩(Kobe Bryant)和凱文.杜蘭特(Kevin Durant),以及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圖博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等人來台時的口譯。當國外有重大事件發生,他也數度臨時受託,在台灣的電視台轉播中為觀眾翻譯,像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2003年美國進軍伊拉克。
徐子超說,身為自由工作者鮮少有機會被人看見,家人也不一定了解自己在做什麼,所以年輕時很珍惜這些機會。「一開始會覺得說只要有曝光、有登上媒體的,這種被看到的會覺得比較興奮一點⋯⋯現在倒過來了,high-profile(備受關注)的場合盡量避免,一不小心,之前的名聲就會毀掉。」
徐子超表示,一般民眾期待的是百分之百完美的翻譯,但現實是,能將8、9成的內容翻譯到位就已近乎神人,而且譯文的精準度只是「專業」的其中一個標準,並非全部:
「學校(口譯教學機構)這邊一直講求的都是要對內容精準、對聽眾負責,但實際工作中,往往不是如此⋯⋯所謂的要對客戶負責,那你的客戶到底是誰?是付錢給你的人,還是在台上的講者,還是其他的單位?到底要讓誰滿意?」
從出道到現在,徐子超服務過的客戶遍及財經、資訊、科技、直銷、汽車、廣告、保險、醫學、媒體等產業,因此他深知不同的情境會產生不同的需求。他舉例說,若一位基金經理人的行程已經延誤,可能會期待口譯員盡可能地摘要演講內容,而不是追求一字不漏的翻譯;在美國進軍伊拉克的轉播中,畫面上就算沒有明顯的動靜,他也須統整零碎的外媒消息,以記者的口吻為觀眾說明事件發展。
換言之,口譯員在工作時,經常夾在多方的利益考量之間,受到諸多因素的牽制,甚至要游移於不同的角色。但徐子超表示,一旦成為眾矢之的,就算有理也說不清,碰上政治還會被貼標籤,累及未來的職涯。位居快要退休的階段,他已不打算再承接危機四伏的工作,因為假如接了下來,「最好的結果就是『沒事』而已,只會往下,不會往上⋯⋯吃力不討好啦,簡單說就是這樣。」

以承攬形式接案的自由口譯員,遇到「燙手山芋」可以推卻,但任職於政治和外交領域的口譯員無法迴避風險,亦無法靠個人的力量扭轉社會氛圍。
「我現在很佩服還繼續在外交部工作的同仁,我真的覺得他們的抗壓力好強好強,因為隨便什麼會議都是線上直播,然後就會有這個全民公審。」曾在外交部任職的陳珮馨笑著自嘲:「還好姊姊出道得早!」
陳珮馨擁有台師大翻譯研究所、英國巴斯大學翻譯研究所雙碩士,2009年經由考試成為外交部翻譯人員,平時若有外國貴賓來台拜訪各部會,她便居中提供口譯服務,另外也要筆譯各種致詞和演講稿。而在她工作的6年期間,陳珮馨總共為時任總統馬英九做過近2,000場口譯,被外界譽為「總統級口譯」。
在政治和外交上,用字遣詞涉及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口譯員必須格外敏銳才不致釀成風波,但也不能死守字面上的忠實,必須掌握訊息背後的意義。有「日本口譯界第一把交椅」封號的長井鞠子就曾在著作中提到,在1980年代日美貿易談判中,有官員悄悄提醒她勿翻譯得過於果斷自信,因為日方雖然在口頭上提出多項措施,整體態度卻偏向敷衍。
在這個高度敏感的領域生存下來極為不易,但陳珮馨受訪時並未多提當年勇,反倒大方分享一些小失誤。例如,馬英九有次對外賓說,台灣役男每天要跑3,000公尺,她在翻譯時望著筆記上的 “meters”(公尺),卻不小心講成 “miles”(英里)。
從自身經驗出發,再談到口譯員在直播時代動輒得咎的問題,陳珮馨鄭重提醒:
「世界上沒有所謂『完美的口譯』⋯⋯口譯員難免就像是不小心自己講話吃螺絲,或者是有一些聽不懂的地方,之後再事後糾正,我覺得這個就是家常便飯,大家就請以平常心(看待)。口譯員是人,口譯員不是機器,口譯員也不是神。」
事實上,就算是機器也有出錯的時候。陳珮馨離開外交部後,除了擔任自由口譯員,也從事新聞播報和主持工作,而她近期主持過一場會議,主辦單位捨棄真人口譯員,改用語音辨識軟體及翻譯軟體把演講內容轉換成中文字幕,但過程中,“CBAM”(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被辨識成“seabed”(海底),於是整場演講不斷湧現海底的各種事物。
但相較於真人口譯員經常受到嚴厲審視,陳珮馨發現,現場沒有人向主辦單位反映AI翻譯的錯誤。
「是因為它還是一個噱頭嗎?是因為你覺得它還在進步嗎?」陳珮馨呼籲大家思考:「為什麼你對機器可以這麼的寬容,甚至會覺得『哇,好可愛喔!』拍起來變成一個哏圖跟好朋友分享,而對於一個認真、兢兢業業準備的人類口譯員,可能只是不小心口誤,或者說可能哪裡不小心不如你的意,你就要上網大動肝火,可能要發一個文去罵他,然後還要跟其他的人筆戰?」
陳珮馨強調,她認為有建設性的指教很好,但若批評只是為了展現自己的優越感,則大可不必。
如果將容易引發爭議的場合比喻為燙手山芋,那麼在口譯界的「燙手山芋排行榜」上,總統勝選國際記者會絕對名列前茅。
2020年和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分別由蔡英文和賴清德勝出,兩人都在開票當晚召開國際記者會,現場有國內媒體進行實況轉播,還有來自數十國的上百家外媒嚴陣以待。口譯員要傳達當選人的致詞,也要翻譯媒體提問與當選人的回應,短短40分鐘的記者會看似在固定框架內運作,實則驚險刺激。
連續兩次接下這份工作的口譯員,是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范家銘,他曾獲邀至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院(MIIS)擔任訪問教授,現為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副理事長。在20年的口譯生涯中,他以金融、科技、公衛和醫療類型的會議口譯為主,但早期工作時也經常接觸到台灣加入(重返)聯合國等政治相關的議題。
「雖然可以依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知道,總統當選人致詞一定有稿子,可是問答呢?記者會問什麼?勝選人會怎麼回答呢?場地聲音會不會因為很吵雜而聽不清楚?我會不會上鏡頭?會不會在網路上又因為意識形態和政黨屬性不同,受到各種批評謾罵?認識我的人會不會覺得『原來你是幫哪個政黨工作』,我就被貼了一個標籤,說是OO黨口譯員?」
范家銘憶及2020年,他在總統大選的3天前接獲委託,內心經過一番掙扎,也權衡過各種利弊,但最後仍選擇答應:「好像就是使命感吧,就覺得這件事情我有很高的機率可以做好,既然如此,人家願意給我這個機會,我就好好把握。」
接著,他火速展開一連串的準備,包括回顧蔡英文過去的演講和訪談,尤其是選前幾個月對外媒的發言,從中熟悉蔡英文的思路;為了維持中立形象,他也斟酌服裝的顏色,最後選擇粉紅色襯衫和紫色領帶,以避開不必要的政黨聯想。
到了投票日,他白天便去勘查記者會現場的桌椅、視野、燈光、音響等細節,並且在試音過程中,請工程師在他的位置附近加裝監聽喇叭,以便聽見最清晰的聲音;傍晚收到雙語講稿後,他開始反覆練習、印出紙本標註換氣斷句的地方,而講稿中途也歷經數次調整,須隨時配合更新。在記者會召開前不到一小時,他拿到記者提問的中文參考資料便立刻研讀,並上網查找官方或英文用語。最後,這場記者會平安落幕。
2024年,同樣也是臨時受託,范家銘再次為總統勝選國際記者會翻譯。但這次不同的是,《TVBS》隔日播出一則新聞:〈國際記者會口譯頻出包 蕭美琴銳利眼神關切 賴國安團隊雛形、人選受矚目〉,內容旨在探討新政府的國安團隊組成,途中卻話鋒一轉:「尤其當選的國際記者會上,找來的口譯不OK」,同時,畫面左上角出現「團隊出包能接軌?」的字樣。
新聞播出後,《TVBS》記者在個人Facebook粉絲專頁上,進一步指稱口譯員「誤譯」、「超譯」,引發許多翻譯界人士留言表達不滿,並提出有關口譯的討論。數日後,《TVBS》在原報導附上說明:「經重新檢視內容與標題,新聞部認為電視標題中『國際記者會口譯頻出包』用詞過重。雖有觀察討論空間,但頻出包作為標題並不符合比例原則,謹此更正。」如今,該則新聞的標題已刪除提及口譯的部分,但影音和全文內容仍原封不動。

對此,范家銘受訪時表示,有關中美之間的“increased tension”,「我承認如果一開始就翻成『衝突升高』的確就是沒什麼問題,但我並不覺得講了『中美戰爭』,然後補充了『中美貿易戰』,這樣會讓人有任何誤會。」他指出,在《彭博社》記者提問的語境裡,衝突升高跟中美貿易戰本質上是一樣的事物。
他也說明,之所以講了中美戰爭,又立刻補上中美貿易戰,就是因為意識到戰爭二字恐造成誤會,於是立即修正。至於當下為何未想到「衝突升高」四個字,他思索著說,「可能是覺得那時候他的問題有非常多的細節,我自己回頭看筆記是很完整,正是因為完整,當下處理的時候有一點點被字詞綁住⋯⋯你要說錯,我也不能說這樣講很不公平。但這樣的翻譯真的是『錯』的嗎?」
至於「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翻譯,他指出,主辦單位提供了中英文講稿,「(英文)原稿就是這樣子寫,我就是照著指示念,今天被人家說是『誤譯』⋯⋯我覺得在這種場合裡頭,口譯員通常都會是代罪羔羊,所以我當下其實也不覺得這個有多大不了,不會覺得很委屈或生氣。我能夠理解我被怪罪這件事。」
當多數人對於翻譯的想像是「逐字對應」,且忽略政治場域的微妙運作時,口譯員的處境便格外艱難。 無論如何,范家銘表示,他未來不會因為此次風波就刻意避開某些挑戰:
「我們就是繼續把該做的工作做好⋯⋯當每個人都很努力地提供最好品質的服務,其實就會讓市場上使用口譯的人知道標準在這裡,這就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大家會彼此督促,愈來愈好。」
范家銘也分享他熱愛口譯的原因,「我們就是很認真在聽每個人講話,也很努力地想要把他們講的話──不管我們認不認同,喜不喜歡──我們想辦法盡量完整地傳達給另一群人知道。另外一群人有沒有想要知道、接收了多少,這也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但我覺得這世界上就是需要有一群非常認真在聽別人說話的人吧。大多數人聆聽的目的都不是為了理解,而是為了回覆。」
口譯員穿梭在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梳理著時而明朗、時而隱晦的意義,然而在協助他人溝通的同時,卻極少有機會與社會溝通自身的專業。或許下一次,當我們有機會在直播中聆聽口譯,可以花幾分鐘思考翻譯背後的挑戰與決策,不是為了留言,而是為了理解。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